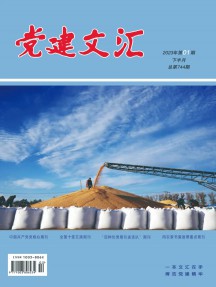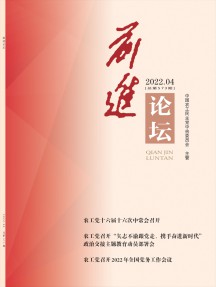政治哲學(xué)導(dǎo)論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4-01-25 15:46:35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蕚淞瞬煌L(fēng)格的5篇政治哲學(xué)導(dǎo)論,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道德;制度倫理;政治哲學(xué);人格尊嚴
中圖分類號:D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3)05―0073―07
康德在道德哲學(xué)中講德行,認為德行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力量;所以人的理性的固有使命不是為了幸福,而是為了更高、更純粹的理想,這就是道德的自主與自律。德行與幸福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不能用幸福定義德行,從直覺上說,這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康德的目的是要克服一切從非理性的沖動而來的動機,讓德行本身發(fā)號施令。而幸福作為一種感受性經(jīng)驗,只是對德行的意識,或者說,德行是幸福的條件,對其本身的意識就是幸福。
當(dāng)然,這里存在著一種矛盾:那種道德的自主與自律一定是能夠?qū)崿F(xiàn)的,否則無法成為人們的道德要求;但它又一定是一個幾乎無法實現(xiàn)的道德理想。這也是一切堅定的道德理想主義者所面I臨的困難。也許有人會說,正因為道德完美只能是理想,才會成為自主與自律的方向;當(dāng)然也可能有人會說,那它就不應(yīng)也無法成為人們的道德義務(wù)。
在康德之后,最先對康德的道德理想提出質(zhì)疑的就是黑格爾。在黑格爾看來,我們不應(yīng)把個人的德行抬得過高,制約人的道德行為的,也許更多地應(yīng)歸因于家庭(親情)、市民社會(友情)和國家(團結(jié))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傳統(tǒng)、法治以及可以通稱為倫理意志的客觀精神。
到了20世紀,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一個現(xiàn)實就是這種德行理論的崩潰。塞瑞娜?潘琳(SerenaParekh)在《阿倫特與現(xiàn)代性的挑戰(zhàn)》中講到阿倫特的20世紀道德經(jīng)驗時告訴我們,歐洲人原先所認為的那種普遍永恒的東西,比如理性,即那種識別對與錯的能力,其實是可以毀于一旦的。于是道德就似乎又回到了其原初的含義――“習(xí)慣”(mores),就是說,道德已經(jīng)成為了一套沒有堅實基礎(chǔ)的習(xí)俗,就如餐桌上的禮儀一樣。
作為背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20世紀是一個殺人不眨眼和死人超過任何一個世紀的世紀。
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現(xiàn)實。阿倫特說,當(dāng)“你不應(yīng)該殺人”轉(zhuǎn)變?yōu)椤澳銘?yīng)該殺人或殺壞人”,而“壞人,,又是一個可以隨時更換的概念時,已經(jīng)不會有任何人表示抗議了。
于是,我們就發(fā)現(xiàn)以后的道德哲學(xué)至少沿著兩個方向艱難前行,一是幸福問題,或者更具體地說,也就是追求幸福這種欲望的正當(dāng)性問題;再就是用人權(quán)取代傳統(tǒng)的德行或良知,為道德規(guī)范重新提供一個主要的基礎(chǔ)。講人權(quán),主要是針對強權(quán)而言的,因為20世紀給我們的一個基本教訓(xùn)就是必須抑制權(quán)力的為所欲為。所謂的“殺人不眨眼”大都與權(quán)力的運作有關(guān),甚至自然災(zāi)害或貧富差異也蘊含著社會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于是追求權(quán)力的欲望(當(dāng)然權(quán)力本身不會是空洞的東西)也就壓倒了所有其他一切的欲望。拉康的“欲望倫理學(xué)”就是要讓主體把自己的無意識(那里一定積壓著諸多的欲望)清理出來,好好地說出來。這既有臨床的意義,要解決人類文明中的癥狀,也通過把外在的社會規(guī)則的制定者命名為“大他者”,而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無意識正是“大他者”的語言效果,而我們只不過是這種語言的傀儡而已。傳統(tǒng)的德行與良知學(xué)說在理論上總與某種神圣的或者具有超驗之源的內(nèi)在經(jīng)驗有關(guān);這種內(nèi)在經(jīng)驗所依賴的,就是西方自中世紀以來漫長悠久的自然法或自然權(quán)利學(xué)說。那時候,外在的規(guī)范與強制性戒律(自然法)、內(nèi)在的反省(良知或德行)是完全一致的。今天,外在的規(guī)范與強制性戒律(自然法)崩潰了,剩下的就只有內(nèi)省的主觀經(jīng)驗。也就是說,一方面,這種內(nèi)省的主觀經(jīng)驗喪失了其神圣而超越的外在依據(jù),另一方面,它又同時告訴我們,所謂的道德,必須完全與外在的服從相分離。道德一旦變成了對外在力量的屈從,便不再有道德可言;這種屈從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偽善。偽善幾乎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無法解脫的道德之困,此即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所謂的“鄉(xiāng)愿,德之賊也”。“無論是上帝之法,還是國家之法,我們必須在法律與道德之間進行區(qū)分。”分離后的道德也不全靠內(nèi)省,而是被置于與他人的關(guān)系之中。阿倫特告訴我們,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個道德箴言均與他人相關(guān):“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之所欲,當(dāng)施于人”;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康德的道德絕對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時認為也能為所有人認可從而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去行動,這就是自己必須與自己相一致(不矛盾律),因為自己同時在為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東西立則。
于是,道德的根基不再源于某種神圣的或者具有超驗之源的內(nèi)在經(jīng)驗,它事實上來源于語言在沉積中構(gòu)建而成的“自我”,來源于那種人所固有的社會關(guān)系也就是與他人的現(xiàn)實關(guān)系之中。
如果要講內(nèi)在經(jīng)驗或者講德行與良知的話,它也就應(yīng)該在與“自我”(拉康命名為“小他者”,即另一個與“我”相似的“我”)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以及與他人的外在關(guān)系這一前提下更內(nèi)在化、主觀化為一種對尊嚴的意識。
康德說:“目的王國中的一切,或者有價值,或者有尊嚴。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能被其他東西所代替,這是等價;與此相反,超越于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代替的,才是尊嚴。”
康德進一步區(qū)分了市場價值(與人們的普遍需要有關(guān))、欣賞價值(與人們的無目的情趣相適應(yīng))與尊嚴。前二者都是相對價值,只有尊嚴才是“構(gòu)成事物作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條件的東西”,這里顯然就指的是生命;或者說生命本身就應(yīng)該有它自身的尊嚴。
只有生命的存在才是絕對的,它不似人權(quán)或權(quán)利學(xué)說那樣在與義務(wù)的相對性中討論問題,而是把某種具有絕對性的自在目的作為了一切權(quán)利的前提或條件。
在阿倫特的書中,多處地方談到了生命或某些人的生命,某一種族、某一階層、某一群體的生命為什么在某種情況下會被視為了多余。
那些被視為了多余的生命首先喪失的就是尊嚴;而他們在萬般無奈的境況下唯一可維護的,其實也只有自己的尊嚴。徐賁先生在為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化學(xué)家和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所著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3年)所寫的“導(dǎo)讀”《幸存者的記憶與見證》中說,在萊維那里我們看到了一種“平凡美德”,一種“弱勢美德”;這種美德就是在經(jīng)歷了地獄之火,已經(jīng)變得十足的謙卑而現(xiàn)實的同時,卻依舊懷有羞恥心,懷有自尊感,拒絕就此墮落下去。所謂“弱勢美德”,是相對于“強勢美德”而言的。“強勢美德”常與歷史進步和公民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而“弱勢美德”則總是伴隨著被侮辱、被損害、被踐踏的弱者經(jīng)歷,它不能使人成為英雄,也無法讓人充分高尚,至少不是康德意義上的道德高尚,而是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帶保持那種人之為人的最起碼的尊嚴,不至于完全絕望或徹底墮落。
當(dāng)我們今天談到道德、制度倫理和政治哲學(xué)時,都應(yīng)該首先確立自己作為一個“平凡美德”或“弱勢美德”的立場;這等于先要承認自己其實無法認識或掌控歷史的進步,甚至至少在眼下還無法實現(xiàn)公民政治的,剩下的就只有了個人的尊嚴和彼此間在尊嚴問題上的相互溝通與彼此維護。于是從這里就可以引申出制度倫理與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
康德其實也已經(jīng)意識到了盡管德行是唯一內(nèi)在的善(德行完全依賴于自身,無論條件是如何的不利,德行總是能夠?qū)崿F(xiàn)的),但卻不是至善;“至善由擁有相應(yīng)數(shù)量的幸福的德行構(gòu)成。”這里的“相應(yīng)數(shù)量’’就說的不是個人,而是“共同體中的總體善”。從邏輯上講,“至善”同時也應(yīng)該是一個既包含了完美德行同時也實現(xiàn)了最高幸福的概念。布勞德(Charlie Dunbar Broad)在他的書中區(qū)分了“共同體中的總體善”與“共同體的總體善”這兩個概念,這比較有意思。前者說的是共同體中所有人的善(或理解為利益、幸福)的總和,后者說的是共同體(富國強兵之類的愿景)自身的善。如此看來,康德所講的“相應(yīng)數(shù)量的幸福的德行”就指的是“共同體中的總體善”,而不是“共同體的總體善”。在布勞德看來,“共同體的總體善”依賴于“共同體中的總體善”;這種依賴部分指的是“如何分配共同體中的總體善的方式”(羅爾斯就是想回答這一問題),部分指的是共同體中成員間的相互關(guān)系(沿著胡塞爾的“生活世界”與“主體間性”一脈相承下來的所有問題)。
在拉康看來,如果說“善”與個人“道德”有關(guān)的話,“至善”就指的是“倫理”意義上的“善”;也就是說,如果說“善”是個人的自我約束的話,“至善”則是自我約束的參照,也就是說,約束個人的東西其實來自于某種普遍性的、約束著所有人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什么呢?一是決定著個人習(xí)慣養(yǎng)成的習(xí)俗、傳統(tǒng)、文化;二是社會性規(guī)范(最具有強制性的無疑就是體現(xiàn)國家意志的制度、法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具有普遍性品格的文明秩序,它與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當(dāng)然也有著更多的關(guān)聯(lián);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至善”這一概念所要告訴給我們的那種道德理想。在康德這里所講的“道德”之所以在黑格爾那里會變成“倫理”,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康德的個人意義上的道德理想其實不得不參照或不得不來源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意義上的普遍倫理;國家不過是這一普遍倫理得以實現(xiàn)的載體而已。在拉康看來,“至善”其實也就是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所講的“實在”,它無法觸及,但又具有無比的吸引力,“因為善的領(lǐng)域正是圍繞著這個完全不能觸及而又具有吸引力的中心組織起來的。”拉康接著說,“問題在于,要將實在作為‘空’來認識理解,并通過欲望和時間的辯證法來思考實在。”
倫理意義上的“至善”其實不過就是一個“空”。黑格爾在《邏輯學(xué)》中經(jīng)常將上帝、關(guān)于法律和倫理的原則相提并論,并告訴我們?nèi)祟愰_始思維時,只能從沒有任何規(guī)定性的“有”(純有)開始,而這樣的“有”其實也就是“無”,因為它沒有任何具體的規(guī)定性。王海明教授在他的《(國家學(xué)>自序》中專門提到了時的“公字化”與“忠字化”運動,全民性地大立“公”字、“忠”字,大破“私”字、“我”字,人人都要做到“三忠于、四無限”。但這里的“公字化”、“忠字化”運動中的“公”與“忠”,不過就只是兩個空洞無物的“字”而已,誰都無法做到,但又具有無限的吸引力,致使全國人民都處于某種癲狂狀態(tài)之中。除了不得不的外在使然,也與“主體對自己的欲望一無所知”有關(guān),于是欲望(完全做到“三忠于、四無限”)就在一條長長的能指鏈上奔跑,“并且通過一個阻止固著的無可救藥的不滿意,被一個根本性t不是這個’所標記,于是乎,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由于沒有人能做到,所以也就沒有人(包括自己)滿意,它的唯一作用就是“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
我們每個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應(yīng)該仔細想想,“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這到底是什么意思,對我們來說又是多么的真切。
于是,我們也就更理解了我們的世界其實是用語言建構(gòu)起來的,特別是倫理意義上的“至善”,比如“公”、“忠”,比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它超越了所有具體的、個人道德意義上的“善”,成為了具有“至善”意味的外在強制。統(tǒng)治者是一定會通過一整套的制度和實際的軍隊、法庭來維護這種有利于自己統(tǒng)治的“至善”理念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它導(dǎo)致的也一定就是偽善。從理論上說,離開了“至善”,我們無法規(guī)定具體的、有形的“善”;但離開了這些體現(xiàn)在具有個人自主精神的人身上的具體的、有形的“善”,所謂的“至善”不過就是一個“空”。“至善”作為“空”,否定著所有具體的、有形的“善”(“不是這個”);而所有具體的、有形的、不是這個或那個的“善”的總和又在實際上實現(xiàn)著一開始必定是空洞無物的“至善”,這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拉康說要“通過欲望和時間的辯證法來思考實在”,其實也就是要遵循著黑格爾的思路來理解作為“空”的“實在”是如何成為了“實”的“實在”的。這當(dāng)然也是一個漫長到幾乎看不到盡頭的過程(所以才有了后來的“過程哲學(xué)”)。如果我們能從主奴關(guān)系的角度理解無限的“空”(主人)與有形的“實”(奴隸)的關(guān)系,也許會使問題變得更為清晰。納塔莉?沙鷗在講到拉康的學(xué)說時,專門提到1933年至1939年間,拉康曾專門跟隨亞歷山大?科耶夫閱讀黑格爾,閱讀的線索就是欲望問題;人的欲望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價值的追求,“如果價值沒有被他人認可,那么欲望也就迷失了方向”。所以,首先,欲望完全是被認可的欲望,欲望本身需要如此被承認;其次,主人的位置一定會在奴隸們“為承認而斗爭”的過程中受到嚴重動搖。當(dāng)然,動搖或改變的結(jié)果很可能就是奴隸變成主人,而原來的主人則淪為奴隸。在霍布斯看來,最初之人是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尼采認為,最后之人則是最終獲得了勝利的“奴隸”。
于是,主人們?yōu)榱瞬恢率棺约簻S為奴隸,有兩條路可循:一是強化暴力鎮(zhèn)壓的力度,二是必須“對于制度進行價值審視,以制度的‘善’為核心,分析與揭示制度的道德價值屬性及其具體內(nèi)容”。設(shè)法對制度本身進行價值審視,以從根本上滅除主奴之別,這種制度化的保證就是高兆明教授所理解的“制度倫理”,亦即他所理解的“正義”。當(dāng)然,它的前提必須是:第一,任何正式的國家制度本身就具有倫理屬性;其次,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一定離不了人的“自由”與“實踐”。納塔莉?沙鷗認為拉康更強調(diào)的是人的“意識”,因為人總是要有意識的,而“意識”(conscience),無論在英文還是在法文中,本身就具有道德層面(好的意識即良知)與認識層面(正確的認識即真理)雙重意思。“有意識”,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就指的是“故意”或“有價值取向”。這也就是說,“理論”(求真)與“實踐”(求善)并不是兩張皮,而是人的意識活動本身的兩種屬性;而人的意識活動本身就是自由的,這似乎本來就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什么東西都無法限制也限制不了的簡單事實。所以自由應(yīng)該是討論自尊、道德、制度倫理、主體間溝通與交流等所有問題的最底層的要求或前提。
“有意識”,到底其意何在?現(xiàn)在大多講“承認”,這是從黑格爾那里來的;但承認,用《(世界人權(quán)宣言>前言》中的話來說,就是追求“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內(nèi)在尊嚴以及平等與不可讓渡之權(quán)利”,并認為這才是自由、正義與世界和平的基礎(chǔ)。“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這個概念雖說來自西方,但也是中國古代的先賢們反復(fù)強調(diào)的一種“君子風(fēng)范”,如“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孔子),“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荀子),等等。
現(xiàn)在的問題只是要討論:為什么主奴關(guān)系的制度本身并不是善,以及如何才能使要求承認的欲望(要有人格尊嚴的欲望)在制度上受到保護的問題;當(dāng)然,它也不可能只限于“君子”,而是指“大家庭中所有成員”。
到底什么是政治哲學(xué)所要研究的問題?早已眾說不一;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政治事關(guān)眾人,事關(guān)共同體的存在、運作方式,所以也就與共同體中的每個人都有著切身的關(guān)系;它所要保護或維護的就是每個人都應(yīng)該具有相同的自由的機會與能力。但現(xiàn)實生活中卻并非每個人(或因種種外在因素的限制或不愿意、不允許)在機會與能力上都是均等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參與到政治的活動之中。政治活動需要作出判斷,所以阿倫特才認為《判斷力批判》包含著康德政治哲學(xué)最偉大與最原創(chuàng)的部分。①她認為政治與審美歸根結(jié)底是結(jié)合在一起的,它們都源于“主體間性”這一概念,也就是自胡塞爾以來的現(xiàn)象學(xué)一脈。塞瑞娜?潘琳解釋說,《實踐理性批判》之所以與《判斷力批判》(盡管康德或其他更多的人均想從道德學(xué)說發(fā)展出政治學(xué)說)不同,就在于前者的“絕對命令’’建立在一個人不應(yīng)與其自身相沖突的觀念之上;而后者所講的“判斷”則涉及到共識的達成,所以它不是個人的思考,而是“必須將自己從主觀的、私人的狀況與特質(zhì)中解放出來,就是說,一個人必須超越其個體局限性,以便考慮其他人的立場”。政治與審美都需要通過對判斷的分析來理解一個對共同世界的共通感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判斷與審美判斷的主觀普遍性相似,既非完全主觀,也非完全客觀;“這個雙重性有助于我們通過表現(xiàn)這個‘主觀普遍性’空間的重要性來理解共同體的世界。”阿倫特政治哲學(xué)的全部努力就是要重建一個與現(xiàn)代性相適應(yīng)的公共領(lǐng)域的本體論意義;這個公共領(lǐng)域的重建又離不了人與人之間的共通感。共通感不同于私人感覺,而所謂的“私人感覺”事實上又只能求助于共通感。鑒賞判斷中的“這使我愉快”就扎根于共同體的經(jīng)驗之中,并因此走向一種開放溝通的心態(tài)。可溝通性依賴于一個開放的心態(tài),共通感是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條件與結(jié)果。
在《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告訴我們,極權(quán)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恐怖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人孤立,當(dāng)所有的勞動都只是為了活下去時,孤立就變成了孤獨;而孤獨是一種根本不屬于世界的感覺,“這是人類經(jīng)驗中最徹底、最絕望的一種經(jīng)驗”。塞瑞娜?潘琳說,“無根”意味著“在世界中沒有立足之地,不受他人的認可與保護”,“多余”意味著“根本不屬于這個世界”,而“無世界性”則可以界定為共通感的喪失。許多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是因為他們成為了事實上的“孤獨個人”,于是也就喪失了本屬于階層或共同體才有的尊嚴。而那些故意炫耀權(quán)力與財富的人,也是因為他們把自己視為“孤獨個人”,于是只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他人的承認。對每個人來說,共通感都是這樣一種感覺,它“規(guī)范并控制其他所有感覺,如果沒有它,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封閉在自己特殊的、不可靠的感覺材料之中”。如果人權(quán)的本體論基礎(chǔ)是其所呈現(xiàn)的多樣性,以及它只有通過我們的判斷而持續(xù)存在的話,那么在現(xiàn)代性中,公共領(lǐng)域的衰落對于人權(quán)來說就具有了如此的毀滅性。
其實政治哲學(xué)的根本意向就涉及到一個公共領(lǐng)域的重建。從理論上講,這里面又涉及到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公共領(lǐng)域是如何喪失的,再一個就是主體間性、他人、承認、尊嚴,即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道德與制度倫理,對于公共領(lǐng)域的重建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
在古希臘的城邦,世界被明確劃分為公共與私人兩個領(lǐng)域:家庭屬于私人領(lǐng)域,家庭也提供了欲望的基本需要與滿足,勞動與制作的地點就在家庭的領(lǐng)域之內(nèi);而廣場則是公共活動的領(lǐng)域,它是在與他人一起言說與行動中展現(xiàn)出來的。前者受著必然性(或理解為生活必需品)的驅(qū)使,后者則是一個自由的領(lǐng)域;受必然性驅(qū)使是前政治的,因為它只能以暴力的形式獲得解脫;所謂的“自由”,就指的是不再為謀生或維持生命而奔波,自然,在古希臘的城邦,那些衣食無憂的人都是一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為后來的貴族。而政治從來不僅僅是為了生存,它是為了生活,或為了讓所有的人都能從前政治的必然性的驅(qū)使中解脫出來。這也是革命不得不發(fā)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這種解脫的一個結(jié)果就是公共領(lǐng)域與私人領(lǐng)域在界限上的消失,因為“社會”的出現(xiàn)同時取代了家庭和廣場;原本屬于私人的事情變成了公共的事情,而所有人的平等(同質(zhì)化的同一)則取代了原本屬于貴族們只有通過政治參與才能獲取的平等,同情取代了尊重,人民取代了公民。這里面重要的地方在于對“同質(zhì)化的同一”的理解,因為這種“同質(zhì)化”在消滅了多樣性的同時,也毀掉了個性、特征這些努力要使自己表現(xiàn)得卓越的“客觀聯(lián)系”,因為隨便“你做什么對其他人來說都沒有影響,或者從字面上來說,沒有興趣”。這當(dāng)然也就意味著一個可政治參與的公共領(lǐng)域的消失。政治成了一個單純地想達到什么目的,于是只能在手段與目的框架內(nèi),以成王敗寇為價值取向的少數(shù)人最后化簡為一個人的活動。所以西方的政治哲學(xué)史家大都認為在希臘化、古羅馬時代是無政治可言的,因為沒有了眾人的參與。但這并不等于就沒有了個人的尊嚴。尊嚴來自于基督教的世界觀,基督教的一個核心信念就是普遍的人類尊嚴。這同時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基督教是站在被侮辱、被損害與被踐踏的弱者一邊的;他們沒有權(quán)利可言,也幾乎沒有人權(quán)的概念與意識,有的就只是尊嚴。這同時說明了,為什么在阿倫特眼中,并不存在天賦人權(quán)、自然權(quán)利之類的東西。塞瑞娜?潘琳補充說:“只有當(dāng)人類尊嚴向現(xiàn)代性挑戰(zhàn)的時候,人權(quán)才會表現(xiàn)為捍衛(wèi)尊嚴的一種方式。在這一意義上,人權(quán)是對人類尊嚴的特別墮落的一種反應(yīng)。”國家當(dāng)然是人類需要的產(chǎn)物,當(dāng)維持并壓制住社會的同質(zhì)化同一并繼續(xù)壟斷政治領(lǐng)域的公共空間時,那即是阿倫特所理解的極權(quán)主義了。
這里面可能導(dǎo)致兩個問題:一是在現(xiàn)代性危機的總體背景下,人們是否又表現(xiàn)出某種渴望回到古代社會的精英主義立場?二是在中國式的、古代傳統(tǒng)的家國體制下,家庭這一必然的、暴力的、前政治的欲望滿足方式是如何演化為現(xiàn)代性中的中國政治模式的?我們是否能按照欲望的滿足(比如承認問題,比如尊嚴問題)從“是”中推論出價值的“優(yōu)劣”?按照王海明教授在《國家學(xué)》中的分析,國家本來不過是社會的下位概念,即國家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但由于國家又是擁有最高權(quán)力的社會,所以便具有了可怕的強制性力量。這種力量作為一種欲望,也需要獲得承認。獲得誰的承認?自然是該社會成員的承認。與此同時,王海明教授再引用鄧初民的話說:“政府不過是執(zhí)行政治任務(wù)、運用國家權(quán)力的一種機關(guān)罷了。”但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最習(xí)以為常的,恰恰是政府代表著國家,國家代表著社會:也就是執(zhí)行機關(guān)(政府)取代了它的(國家),而又取代了它的委托者(社會)。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這里都存在著一種顛倒。在此顛倒下,承認就發(fā)生了顛倒,個人的尊嚴也就變成了不得不讓別人臣服的尊貴。
既然社會的興起以及公私兩領(lǐng)域的衰落是現(xiàn)代性的突出特征,那么如何重建我們的公共世界也就成為了一個現(xiàn)時代的重要議題。阿倫特作為一位現(xiàn)象學(xué)家,也就把對政治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貫穿于她的所有作品之中,而且時時處處不忘“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始意圖。于是,按照胡塞爾關(guān)于“他人就是現(xiàn)象學(xué)的自我變體(modification)”(這幾乎與拉康對于“小他者”的定義一模一樣)的說法,就從“我”與“自我”的關(guān)系(內(nèi)省)擴延為生活世界與主體間的關(guān)系,并把人與人之間的共通感與作為前提和結(jié)果的公共領(lǐng)域聯(lián)系在了一起;而其間的不同于勞動與制作的“活動”、能把人類活動的不可預(yù)測性和不可靠性如其所是地保存下來的“承諾”、不同于自我相統(tǒng)一的“判斷”就使得共通感、共同領(lǐng)域與公共世界的重建在理論上成為了可能。它同時也構(gòu)成為阿倫特政治哲學(xué)的基本架構(gòu)。
最后讓我們引用《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第458節(jié)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jié)束:
篇2
一、古代政治哲學(xué):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
無論是在中國古代哲學(xué)中,還是在古希臘哲學(xué)中,有關(guān)政治問題的哲學(xué)思考都屬于倫理學(xué)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倫理學(xué)的一個分支。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權(quán)威性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為政者必須是善者,這一點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quán)力的政治統(tǒng)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yōu)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tǒng)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quán)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dǎo)致政權(quán)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體的瓦解。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儒家學(xué)說,從其主要內(nèi)容上看,就是一種包含政治學(xué)說在內(nèi)的倫理道德學(xué)說。
在這種學(xué)說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時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學(xué)創(chuàng)始人孔子就直截了當(dāng)?shù)刂赋觯骸罢撸病W訋浺哉敫也徽俊保ā墩撜Z•顏淵》)[1]。其意就是說,為政者必須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惡。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義均是“道義”本身的基本內(nèi)涵。離開了“道義”,不僅無從判斷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的是是非非,而且會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亂,并最終導(dǎo)致天下大亂。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與政治的關(guān)系。
他強調(diào)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現(xiàn)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會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丑上》)[2]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義原則廣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2](488)在古希臘政治哲學(xué)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是最為卓越的。盡管他們二人對諸多政治問題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異,但他們都把“善”或“至善”作為政治活動、國家生活的最高目標,也是衡量政治行為和人的政治品質(zhì)的最終標準,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也是從“善”的理念中獲得最終的依據(jù)。如柏拉圖所說:“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guān)于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3]
柏拉圖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國》中就是把正義作為他的國家學(xué)說的核心理念,這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對正義概念進行理論探討的政治哲學(xué)家。在他看來,一個城邦(國家)主要由三個階層的人構(gòu)成,即統(tǒng)治者(護國者)、輔助者(保衛(wèi)者或武士)和農(nóng)耕商人,每種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適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擾,這是構(gòu)成城邦的原則。所謂“正義”就在于符合這個原則,即“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3](155)同時,正義就是智慧與善。城邦的“正義”主要體現(xiàn)為“智慧”、“勇敢”和“節(jié)制”這三種美德。其中,“智慧”是屬于城邦統(tǒng)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屬于城邦保衛(wèi)者的美德,而“節(jié)制”則是屬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義的城邦就應(yīng)當(dāng)是“善”的,“這個國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節(jié)制的和正義的”。[3](144)柏拉圖還確信,城邦的正義與個人的正義具有一種同構(gòu)性。國家有三個部分,每個人的靈魂也有三種品質(zhì),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當(dāng)人的這三種品質(zhì)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lǐng)導(dǎo)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贊成由它領(lǐng)導(dǎo)而不反叛,這樣的人就是有節(jié)制的人,這種人能夠“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內(nèi)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3](172)
他們能夠帶來城邦的和諧。亞里士多德同樣把“至善”理解為人們組成城邦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學(xué)》一書中,開篇就說:“所有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quán)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4]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4](90)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義”。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為政的準繩。他說:“人一旦趨于完善就是最優(yōu)良的動物,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公正就會墮落成最惡劣的動物。不公正被武裝起來就會造成更大的危險,人一出生便裝備有武器,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們?yōu)榱诉_到最邪惡的目的有可能使用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無德性,那么他就會成為最邪惡殘暴的動物,就會充滿欲和貪婪。公正是為政的準繩,因為事實公正可以確定是非曲直,而這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基礎(chǔ)。”[4](5)
在古代哲學(xué)中,政治哲學(xué)之所以從屬于倫理學(xué),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而言,習(xí)俗、習(xí)慣和道德作為生成和維系秩序的文化機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遠得多。習(xí)俗、習(xí)慣和道德是在人們的共同生活的漫長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為規(guī)則以及解釋這些行為規(guī)則的觀念。這些行為規(guī)則和觀念經(jīng)過長期的演化過程已經(jīng)固化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們心理結(jié)構(gòu)下意識層面中,成為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階級、國家產(chǎn)生以后才形成的社會規(guī)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產(chǎn)生也就標志著文明社會的開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與社會習(xí)俗、道德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由于習(xí)俗和道德構(gòu)成了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須與這些習(xí)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實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過立法程序和政治過程而將那些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總體秩序至關(guān)重要的習(xí)俗和道德規(guī)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習(xí)俗和道德。離開了習(xí)俗和道德,政治問題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權(quán)威性也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quán)力的政治統(tǒng)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yōu)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tǒng)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quán)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dǎo)致政權(quán)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圖之所以在《理想國》中呼吁讓哲學(xué)家出任國家統(tǒng)治者,就是因為他認為真正的哲學(xué)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夠?qū)ⅰ吧啤弊鳛樽约旱膱?zhí)政標準,他們不看重淺近的物質(zhì)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權(quán)力,因而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會良好風(fēng)尚的建樹。
其三,政治哲學(xué)對政治問題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歸根到底來自于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據(jù)并不在于政治活動自身,而在人們最基本的道義原則中。因此,只有倫理學(xué)才能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學(xué)的終極依據(jù)。從這個意義上說,倫理學(xué)構(gòu)成了政治哲學(xué)的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具有絕對意義的“善”,是所有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歸宗。
二、近代政治哲學(xué):道德與政治的疏離
在歐洲傳統(tǒng)政治學(xué)說中,確信“善”與“正義”、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終占據(jù)主流地位。特別是在中世紀,由于宗教神學(xué)和羅馬教會的強權(quán)統(tǒng)治,使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態(tài),即作為“至善”的神是王權(quán)或國家權(quán)力的全部根據(jù)。然而,到了中世紀末期,教權(quán)的腐敗、王權(quán)的專制、教權(quán)與王權(quán)之間的矛盾以及宮廷內(nèi)部圍繞權(quán)力展開的爭斗等等,使人們越來越難以看到,也越來越難以相信政治統(tǒng)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漸對“政治植根于道德”這一傳統(tǒng)觀念產(chǎn)生懷疑。最先對這一傳統(tǒng)政治觀念提出挑戰(zhàn)的是文藝復(fù)興時期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他在《君主論》一書中干脆把政治統(tǒng)治與道德本性剝離開來,提出一種“用目的說明手段正當(dāng)”為原則的政治無道德論。馬基雅維里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從政治理想上說,他崇尚共和政體,認為共和政體有助于促進社會福利,發(fā)展個人才能,培養(yǎng)公民美德。但面對當(dāng)時意大利人性墮落、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的狀態(tài),他認為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社會安寧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他看來,人是自私的,追求權(quán)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jīng)常發(fā)生激烈斗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斗,國家應(yīng)運而生,頒布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君主應(yīng)當(dāng)不圖虛名,注重實際,只要能夠達到目的,無需考慮手段的道德性質(zhì)。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fā),即所謂“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所以他在《君主論》中說,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須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5]當(dāng)君主認為“如果沒有那些惡性,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也就不必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zé)備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著辦了卻能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5](75)這就是說,政治統(tǒng)治的正義是用其最終目的和效果來說明的,一切與此無關(guān)的道德都應(yīng)該被拋棄。基于這種觀點,馬基雅維里明確地把政治學(xué)當(dāng)作一門實踐學(xué)科,將政治和倫理區(qū)分開,把國家看作純粹的權(quán)力組織。可以說,他是近代第一個使政治學(xué)獨立于倫理學(xué)的思想家,因而有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xué)奠基人之稱。當(dāng)然,在近代政治哲學(xué)中,馬基雅維里的這種比較極端的政治學(xué)觀點并不多見。多數(shù)政治哲學(xué)家并不否認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蘊含的道義原則。
這特別體現(xiàn)在近代法學(xué)和政治學(xué)有關(guān)自然法的討論中。所謂自然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如“各有其所有,各償其所負”(格勞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應(yīng)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當(dāng)然,自然法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法律和政治行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為維系社會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沒有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這些基本要求,社會生活就建立不起來,即便建立起來也維持不下去。
但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為共同的生活準則而不致于被個人的任意性所破壞?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貫徹的道德根基?對于這樣的問題,近代思想家則比較普遍地表現(xiàn)出對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認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義的實現(xiàn)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國哲學(xué)家霍布斯從人性本惡的基本立場出發(fā),干脆否認了人憑其本性執(zhí)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來,盡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則,但人的趨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約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須依靠具有強制力的政治權(quán)力。他說:“正義的性質(zhì)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約,而信約的有效性則要在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社會權(quán)力建立以后才會開始,所有權(quán)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6]按照霍布斯的這一觀點,政治的正義與其說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說是為了防范人性的惡。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國哲學(xué)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惡的說法,而是認為人天生就是要過社會生活,這就決定了最初的“自然狀態(tài)”應(yīng)當(dāng)是一種社會生活的狀態(tài),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tài)。在自然狀態(tài)中,人們根據(jù)自己的愿望行動,并受理智的約束,在理性的范圍內(nèi),其行動服從自然的道德律,這就是“自然法”。洛克還認為,在自然狀態(tài)中,每個人都有根據(jù)自然法來懲罰違反自然法的人的權(quán)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賠償?shù)臋?quán)利,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權(quán)利。由此看來,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種道德律,又肯定了個人執(zhí)行自然法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但他同樣認為,政治的正義不可能直接從這種自然法和自然權(quán)利中產(chǎn)生。
因為,盡管在自然狀態(tài)中,人們的行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約束的,但人們的行為卻常常是非理性的,這就造成了自然狀態(tài)的種種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狀態(tài)中,缺少一種確定的、規(guī)定了的、眾所周知的法律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裁決糾紛的共同尺度,從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關(guān)系而心存偏見,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運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狀態(tài)中,缺少一個有權(quán)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zhí)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個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執(zhí)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這就使他們的裁決因情感和報復(fù)之心而超越正當(dāng)?shù)姆秶5谌谧匀粻顟B(tài)中,往往缺少權(quán)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yīng)有的執(zhí)行。這就是說,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們無法解決在理解和執(zhí)行自然法方面所產(chǎn)生的分歧,這就易于導(dǎo)致戰(zhàn)爭狀態(tài)。要避免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就必須走出自然狀態(tài),組成公民社會和公民政府,把每個人執(zhí)行自然法的自然權(quán)利交給這樣的政府,通過頒布和執(zhí)行確定的、眾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來維護自然法和自然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quán)利。他說:“雖然他在自然狀態(tài)中享有那種權(quán)利,但這種享有是很不穩(wěn)定的,有不斷受別人侵犯的威脅。既然人們都像他一樣有王者的氣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嚴格遵守公道和正義,他在這種狀態(tài)中對財產(chǎn)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穩(wěn)妥。這就使他愿意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著恐懼和經(jīng)常危險的狀況;因而他并非毫無理由地設(shè)法和甘愿同已經(jīng)或有意聯(lián)合起來的其他人們一起加入社會,以互相保護他們的生命、特權(quán)和地產(chǎn),即我根據(jù)一般的名稱稱之為財產(chǎn)的東西。”[7]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觀點在近代歐洲政治哲學(xué)的諸多學(xué)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歐洲正處在由以自然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社會向以市場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現(xiàn)代社會的過渡過程中。而市場經(jīng)濟是以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為內(nèi)在驅(qū)動力的,這就必然要求個人的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利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不管這種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利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還是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勞動(如洛克),或者被理解為私有財產(chǎn)制度的產(chǎn)物(如盧梭),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權(quán)利的核心內(nèi)容。
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們看來,要保護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們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將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利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并使之得到有強制力的國家的保護。因而在近代大多數(shù)政治哲學(xué)家看來,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義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總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發(fā)生。這樣,政治思想家們在人們角逐私利的行為中難以相信道德意識本身可以產(chǎn)生積極的政治后果,同時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尋求實現(xiàn)正義的政治途徑。道德與政治之間的這種疏離使政治思想家們越來越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國家政府之類的問題當(dāng)作獨立的研究領(lǐng)域,探討政治過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質(zhì)及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特別是在19世紀后半葉,隨著各門社會科學(xué)的普遍興起,政治問題的研究也逐漸被納入科學(xué)研究的軌道,誕生了作為實證科學(xué)的政治學(xué)。
三、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為政治正義確立道德依據(jù)
當(dāng)政治學(xué)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xué)學(xué)科以后,政治哲學(xué)一度衰落,政治問題的探討逐漸被納入實證科學(xué)的軌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道德問題從政治視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學(xué)主義”思潮的影響,政治學(xué)界一度對政治哲學(xué)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認為政治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價值判斷,沒有嚴格的確定性,只能各執(zhí)己見,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xué),因而不值得重視。這種情況延續(xù)了幾乎一個世紀。應(yīng)當(dāng)說,把政治生活作為獨立的對象,從“事實”的意義上加以研究的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政治生活的總體上說,排除道德問題的或忽視“價值”維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現(xiàn)實的政治活動中,事實與價值是不可分離的。
從客觀事實上說,人類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復(fù)雜的有機體,它在任何一個歷史起點上的未來演化趨勢都具有多種可能性,而哪一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xiàn)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在這種價值選擇中,人們對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平等與自由等道德原則的理解顯然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它決定了人們的歷史活動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驟。正是由于這一點,羅爾斯在試圖通過對政治正義的思考來解決政治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時,也指明了政治哲學(xué)對于倫理學(xué)的從屬性。他說:“政治哲學(xué)有它自己的明確特征和問題。作為公平的正義是針對現(xiàn)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結(jié)構(gòu)這個具體問題而言的一種政治正義觀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圍要比統(tǒng)合性的哲學(xué)和道德學(xué)說狹窄得多,諸如功利主義、至善主義、直覺主義以及其他的學(xué)說。它關(guān)注的是(以基本結(jié)構(gòu)形式存在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不過是道德問題的一部分。”[8]
篇3
《劍橋中國哲學(xué)導(dǎo)論》
【新加坡】賴蘊慧 著 劉梁劍 譯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2月版
要了解中國哲學(xué)的歷史階程,我們一般都會想到的 《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xué)簡史》。尤其是前書,堪為中國哲學(xué)史的奠基之作,幾乎圈定了此后哲學(xué)史書寫的觀念、分期、敘述模式乃至基本看法。不過,的書其實也并不適合做入門書,它的理想讀者應(yīng)是對中國歷史文化有一定程度之理解的讀者。后書雖然最早以英文寫成,但由于學(xué)生有意反對老師,有時難免“為反對而反對”,而另一方面,此書回譯成中文也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了,早期的中譯本很難稱得上是一本入門的理想讀物。從此以后,掰著指頭往下數(shù),最多的就是各種“哲學(xué)史”教材了,不說其他,單說其中概括某一學(xué)說的特征、意義、原理時總要湊上個一二三四點,就有點低估讀者智商的意味。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來說,道家道教滿天飛,究竟何謂“道”?這里我不擬討論“觀念史”研究的成就與局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哈佛大學(xué)宇文所安教授《中國文論讀本》的導(dǎo)言部分),只想指出一點,國內(nèi)通行的教材往往會將各個時期各哲學(xué)家、哲學(xué)思潮分章節(jié)論述,關(guān)于“道”的論述因此就被割裂開去,事實上,各時期的相關(guān)論述隱現(xiàn)不一,且發(fā)端于不同的學(xué)術(shù)潮流,論述重心也頗為不同,如果忽視了這個前提,而且沒有一個圍繞著這個主題進行的比較連貫的、集中的敘述的話,可以想見讀者的認識會多么混亂。那么,怎么辦?拜圖書市場愈來愈強勁的海外中國研究著作之所賜,我們慢慢地就把注意力轉(zhuǎn)到海外學(xué)者身上去了。
最新出版的《劍橋中國哲學(xué)導(dǎo)論》正是這樣一本足以讓我們大致了解中國哲學(xué)的歷史階程、進而游覽西方世界的中國哲學(xué)視景的入門書。全書第一章縱論中國哲學(xué)的起源,并在與西方哲學(xué)比較的過程中闡明中國哲學(xué)的特質(zhì),包括“修身”、“理解自我:關(guān)系與情境”、“和諧”、“變易”、“《易經(jīng)》哲學(xué)”及中國哲學(xué)特殊的論說方式六大方面。其后數(shù)章分別討論孔子與儒家的“仁”、“禮”觀念,孟子和荀子的創(chuàng)造,墨家哲學(xué)與道家哲學(xué),名家與后期墨家,莊子哲學(xué),法家哲學(xué),《易經(jīng)》的精神與影響,中國佛教的思想要義(在印度哲學(xué)中的起源、與中國本土思想之間的交涉、不同派別之間的差別)等中國哲學(xué)史上的一系列關(guān)鍵議題。而對漢朝以后的哲學(xué)家與哲學(xué)思潮的討論,本書付之闕如,至于其原因,除了受制于篇幅,作者亦承認“考察早期中國哲學(xué)的主要概念、主題和文本”最為重要,而其所挑選出如上有代表性的題目意義深遠,在今天仍能激發(fā)連綿不絕的回響。
有人可能會擔(dān)心,當(dāng)孔子遭遇英文,這種“跨語際實踐”的有效性該如何評估,而孔老夫子的偉大觀念會不會歪曲、走樣,《劍橋中國哲學(xué)導(dǎo)論》坦率地面對這樣的疑問,并簡要回顧了這一充滿爭議的論題的始終:早在1983年,華裔學(xué)者陳漢生教授(hansen, chad)在其名著《古代中國的言與道》中就已指出,西方哲學(xué)中的“意義”(meaning)、“概念”(concept)、“觀念”(notion)或“理念”(idea)等詞語無法在中國哲學(xué)中找到相應(yīng)的位置。雖然他的看法沒有被學(xué)界普遍接受,但卻啟發(fā)了一些同人立足于中國固有的思想史背景而討論中國早期語言哲學(xué)、倫理學(xué)乃至元哲學(xué)問題的思路。不過,作者的看法無疑更為公允,結(jié)尾部分她大膽檢討“中國哲學(xué)”的定義,之后又提出界定并且進行“中國哲學(xué)”研究的兩大預(yù)設(shè),即一是不能過分擴張“哲學(xué)”定義,將任何帶有反思性的東西都界定為“哲學(xué)”,二是不能因為急于將中國思想論爭納入現(xiàn)有的西方哲學(xué)概念框架而對它們做出錯誤的詮釋。這兩大預(yù)設(shè),研究者若能時常加以注意,或能洞見中國哲學(xué)的博大精深。本文由收集整理
《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yè)》
徐 賁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中國人喜歡談?wù)撜危皇桥杂^者的看熱鬧和看稀奇。他們猜測、嘲諷、詛咒,始終不過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統(tǒng)治權(quán)術(shù)和陰謀詭計嗎?普通人應(yīng)該積極參與政治嗎?怎樣才能成為“精明的公民”?本書為這些問題提供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
《<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
【美】阿博特·格里森 瑪莎·努斯鮑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編 董曉潔 侯瑋萍 譯
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1999年,為紀念喬治·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芝加哥大學(xué)法學(xué)院舉辦了一場研討會,來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領(lǐng)域的10余位大師級學(xué)者共聚一堂,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寫于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八四》有沒有過時?它對當(dāng)今世界有何意義?
《忽必烈的挑戰(zhàn):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zhuǎn)向》
【日】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
篇4
我們在等待什么?什么在等待我們?
布洛赫:《希望原理》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一位專注于“烏托邦”理想的德國思想家。他探討“烏托邦”的觀念歷史、意識結(jié)構(gòu)、理論形態(tài)和現(xiàn)實基礎(chǔ)等各個方面,在西方思想史上獨樹一幟。然而,正如文森特·喬治甘(Vincent Geoghegan)在《恩斯特·布洛赫》中所言,“布洛赫是一位人們了解甚多、理解甚少的理論家”。當(dāng)我們試圖描述這位思想家時,卻發(fā)現(xiàn)其思想難以定位:
“最后的形而上學(xué)家”(A·施密特),“操馬克思一恩格斯語言的預(yù)言家”(M·瓦爾澤),“一位的謝林”(J·哈貝馬斯),“未來諾斯替主義的者”(L·科拉科夫斯基),“中間世界的思想家”(H·H·霍爾茨),“一位偉大的獨來獨往的人”(I·費切爾)……
當(dāng)布洛赫本人被問及是否屬于哲學(xué)家時,他反向答復(fù)道:“我肯定不是一個非哲學(xué)家,這是很明確的。”實際上,布洛赫的理論體大慮周、縱橫捭闔,大有吞吐八荒,囊括宇宙之氣概;布洛赫雖然堅持自己繼承思想,卻像許多偉大的哲學(xué)家一樣,更愿意人們從更開放的視角去理解他,這也就是為什么N位評論家會看到N種布洛赫面目的緣由。
一、哲學(xué)體系的“夢想”
布洛赫一生筆耕不輟,可謂是一位著述頗豐的思想家,洋洋灑灑的16卷《恩斯特·布洛赫全集》讓人嘆為觀止。實際上,創(chuàng)作偉大的作品,是布洛赫從童年時代就開始規(guī)劃的生活主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洛赫遺產(chǎn)中保留下來不多的記錄本上,專門記錄的幾乎都是關(guān)于全集的事情,關(guān)于各卷的可能的安排,以及各卷的標題的計劃等等。創(chuàng)作大部頭的念頭貫穿于他的一生,躍然見于他的信件:
當(dāng)我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常常夢想,在12月24日黃昏的下午,我為自己已經(jīng)完成的大部頭著作寫上前言。[……]我想要說的是,最美好的生活莫過于此啊,還有就是那從遠方涌動而來的愛之晨光了。
后來,隨著學(xué)習(xí)的深入和生活的擴展,26歲的布洛赫已經(jīng)有意識地計劃寫作多卷本的著作,他在給好友盧卡奇的一封信中,激情昂揚地慷慨陳詞道:
請允許我實事求是、堅決不移地說,我現(xiàn)在正在一步步為我哲學(xué)的榮譽和出版努力;(因為這是無與倫比的偉大事業(yè)),在(那么)一年,在一卷作品之上,我寫上前言,介紹整個方面的現(xiàn)實意義,還有,導(dǎo)論部分包括:邏輯學(xué)和認識論(這兩個是不同方面的剪影和序言,一個藍圖一個非凡的大計劃);在接下來的第一卷:關(guān)于無機自然的哲學(xué)公理;第二卷:關(guān)于有機自然的哲學(xué)公理;接著的第三卷:關(guān)于歷史的哲學(xué)公理;再接著的第四卷:參照哲學(xué)的倫理學(xué)等等;在最后幾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參照哲學(xué)的美學(xué)、教義學(xué)、終結(jié)邏輯學(xué)和公理等等。五卷都有前言和導(dǎo)論以及過渡部分(在第七卷之前),五卷書都有更精確的、舊的長篇部分與前面銜接以及簡單的標題(但是總是以“關(guān)于”為標志等等)。
我們看到,布洛赫初步表達了自己大部頭哲學(xué)著作的觀念,從第一卷到第七卷,對于每卷的內(nèi)容,甚至標題都有所規(guī)劃。那么,布洛赫是不是要像黑格爾那樣,致力于建造一座包羅萬象、自成一體的哲學(xué)大廈呢?
二、理論疆域的“遠征”
事實上,布洛赫本人是堅決反對系統(tǒng)化的哲學(xué)體系的,隨著布洛赫逐步找到自己的哲學(xué)立場,他有意識地要挑戰(zhàn)西方哲學(xué)致力于闡釋概念和營造體系的傳統(tǒng)模式,并不想構(gòu)建一套自我封閉的知識系統(tǒng)。在《主體一客體:評黑格爾》一書中,他檢視過往的哲學(xué)體系,批判揚棄了黑格爾那自成一體、固若金湯的哲學(xué)體系,提出一種新的哲學(xué)體系觀念“開放的體系”,強調(diào)理論“遠征”(Expedition)之重要意義,要理論永葆未完成性和開放性之青春:
即使一個封閉一靜態(tài)的、有所限制的終點,是建立在循環(huán)的循環(huán)上升之上,黑格爾自己還是從那里抽出一種流動性的觀點。也就是說,不同于封閉的體系所具有的自我確證、有條不紊、自成一體三個概念準則,開放的體系需要的僅僅是:遠征。令人吃驚的是,盡管自古以來它就屬于哲學(xué),但是哲學(xué)卻尚未考慮過它。
這種理論“遠征”的開拓性方式在布洛赫最后一部著作《經(jīng)驗世界》中有具體的說明,他這樣總結(jié)解釋道:
真正的結(jié)構(gòu)搭建,使得我們處于完全的創(chuàng)新(Novum)之中,處于一種醞釀著、探索著的時代和世界的創(chuàng)新之中,正是憑借著尚未(Noch—Nicht)的開放性,這種結(jié)構(gòu)搭建也就是一種開放的體系(das offene System)。現(xiàn)在這里所有的著作序列,從《蹤跡》到《經(jīng)驗世界》,都必須與尚未相一致,保持一種斷裂性(Unterbrechung)、細節(jié)性(Details)和拼貼性(Montage);因為不是一切都無可救藥,也不是一切都一無可取。
布洛赫本人所謂“遠征”的“開放體系”究竟如何理解呢?準確地說,雖然布洛赫一直反對哲學(xué)體系,但是他反對的并不是體系本身,而是反對體系的封閉性,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夠打破封閉性保持開放性的哲學(xué)體系,而對于自己著作體系的構(gòu)想,布洛赫哲學(xué)一直是在茲念茲的。如前所述,“斷裂性”、“細節(jié)性”和“拼貼性”就是“理論遠征”的具體表現(xiàn),也是“開放的哲學(xué)”的途徑所在。總之,在布洛赫那里,有意識地規(guī)劃自己的著作體系,同他開放的哲學(xué)體系觀念并不矛盾。或者換句話說,體系并不代表著封閉,開放也并不代表著放開,規(guī)劃體系是有意識地追求開放。
三、思想意味著“超越”
在晚年布洛赫的親自修訂下,1977年《恩斯特·布洛赫全集》在蘇卡普出版社出版,部分卷目的順序相較于年輕時的想法,有了不少改變,更加打破了所謂體系,充滿開放性。《全集》共16卷,每一卷目的內(nèi)容和順序,并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充分體現(xiàn)著布洛赫自己獨特的哲學(xué)體系觀念。
根據(jù)布洛赫的安排,作為引入,第一卷《蹤跡》主要立足于對離奇的體驗、短小的神話傳說以及日常生活瑣事做出闡釋,啟發(fā)我們尋找烏托邦的蛛絲馬跡。接著第二卷《革命神學(xué)家托馬斯·閔采爾》給出一個具體形象的烏托邦符號——托馬斯·閔采爾,然后從現(xiàn)象開始轉(zhuǎn)入論述烏托邦精神,即第三卷《烏托邦精神》(第二版),這一表現(xiàn)主義風(fēng)格的著作對烏托邦精神在當(dāng)代世界的可行性做出理論上的論證,也是布洛赫的第一部代表作。
突然,第四卷《這個時代的遺產(chǎn)》是一個“斷裂”,布洛赫有意識地在著作序列中再次插入類似《蹤跡》的斷片式著作,論述20世紀20年代過渡時期的社會文化風(fēng)貌,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zhì),引導(dǎo)我們在遺產(chǎn)中發(fā)掘希望。然后沿著“遺產(chǎn)一希望”的線索,從現(xiàn)象展開論述,這就是布洛赫的第二部代表作第五卷《希望原理》,它集片斷性、闡釋性于一身,既有回顧也有展望,是百科全書式的自成一體之作。
接下來幾卷,分別是對“希望原理”關(guān)鍵概念的“細節(jié)”展開,如第六卷《天賦人權(quán)與人的尊嚴》、第七卷《唯物主義問題的歷史與實質(zhì)》與第八卷《主體客體:評黑格爾》專門闡釋“具體烏托邦”主題;第九卷《文學(xué)散論》論述“陌生化”主題;第十卷《哲學(xué)散論》論述“客觀想象”主題;第十一卷《政治論集》論述“政治烏托邦”,同時還與《這個時代的遺產(chǎn)》形成上下文對照關(guān)系;這些材料,部分是準備、部分是補遺,都在細部應(yīng)和了“遺產(chǎn)希望”線索。
再接著兩卷是一種“拼接”,又是一次理論的深入,一卷是探尋“希望原理”的哲學(xué)史,即第十二卷《哲學(xué)史里的中間世界》;另一卷是作為“希望原理”的理論緒言,即第十三卷《圖賓根哲學(xué)導(dǎo)論》。如果不理解布洛赫的理論立場,很容易誤會這兩卷放錯了地方,因為按照一般的哲學(xué)體系,這理論性、導(dǎo)論性的兩卷顯然應(yīng)該放在《全集》之首;事實上,布洛赫強調(diào)理論的“遠征”,這種斷裂和拼接是希望保持思想的開放性,而不是讓人們先入為主去立論,然后展開,最后結(jié)論。
然后,第十四卷《基督教中的無神論》是又一次“斷裂”,前面革命神學(xué)家托馬斯·閔采爾的形象符號在基督教的約伯(Hiob)之處又得到回應(yīng);而這一卷的圣經(jīng)批評,又把《圖賓根哲學(xué)導(dǎo)論》引向更遠一層的終結(jié)之作第十五卷《經(jīng)驗世界》。《經(jīng)驗世界》實際上闡述了開放的體系在范疇上的基本特征,但是這并不是限制哲學(xué)的開放性,而是為了向未來展開。因為《全集》最后一卷第十六卷卻再次出現(xiàn)了《烏托邦精神》,只不過這里是原初的第一版,一切仿佛又回到質(zhì)樸的“起點”,然而卻是為了理論的再一次“遠征”……
正如布洛赫本人所言:
沒有什么是一目了然得要命,或許應(yīng)該看作是一半一半。要有一個順序,但是為了追求自由,為此,順序就必須是斷裂性的。
總之,布洛赫哲學(xué)有一種理論遠征的沖動,是一個開放的哲學(xué)體系。他的一切理論旨歸都指向“超越”。哲學(xué)的門類不是松散地并置在一起的,而是拼合而成的。屬于烏托邦碎片盡管關(guān)系的斷裂但仍是保持著新開放。而與開放的體系相應(yīng),布洛赫采用了獨特的文體風(fēng)格,片斷式的寫作方式。他的作品遍布著晦澀不明的隱喻,無法翻譯的雙關(guān),模糊難懂的措辭以及夸張渲染的修辭,正如他終其一生都在強調(diào)“尚未”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布洛赫的理論本身具有未完成性和開放性,這也是時至今日布洛赫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和當(dāng)下價值的根源所在。
結(jié)語
對于拒絕封閉和界限的布洛赫來說,開放的體系使我們不得不打破傳統(tǒng)的理論界限和文體分類,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它。布洛赫既是哲學(xué)的又是文學(xué)的,既是認知的又是審美的,實際上,布洛赫是超越哲學(xué)和文學(xué)、美學(xué)的,甚至是超越神學(xué)的,無論是哲學(xué)還是美學(xué),都有一種超越現(xiàn)實超越自我的企圖,布洛赫把我們引向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獨一無二的布洛赫世界。
閱讀布洛赫就是一次冒險的奇幻旅程,就是一次超越的思想歷程。
篇5
一、蘇格拉底政治哲學(xué)的哲學(xué)基礎(chǔ)
(一)德性論。前蘇格拉底時期的思想家關(guān)注自然事物,探討宇宙的規(guī)律,蘇格拉底則認為除了自然科學(xué)知識,還有一種關(guān)于人和人性的知識,他開始探究關(guān)于人的學(xué)問,關(guān)注知識與美德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要探究關(guān)于人的知識,就是要“認識你自己”。我們所能探討的知識是關(guān)于人的德性的知識,德性包括了正義、虔誠、忠誠、勇敢、公民義務(wù)等。從德性論角度看,蘇格拉底將人們追究事物意義的視線從天上拉回了人間,具有了西方古典人文精神,實現(xiàn)了古典人文精神的一次大轉(zhuǎn)向,他明確提出了我們不需要探討自然事物的意義和本質(zhì),而應(yīng)探討“人”的意義。
(二)方法論 。蘇格拉底將關(guān)于自然事物的本原放在括號內(nèi)懸置起來,而關(guān)注德性知識,這具有現(xiàn)象學(xué)的意義。蘇格拉底的助產(chǎn)術(shù)也就是強論證法或者說是誘導(dǎo)論證法具有很深遠的意義,智者運動就是教人們?nèi)绾斡脧娬撟C戰(zhàn)勝弱論證的,蘇格拉斯誘導(dǎo)的概念主要是與政治哲學(xué)有關(guān)的,例如正義、德性等。蘇格拉底用這種方法探討了公民的義務(wù)和責(zé)任,公民不服從理論等公民政治哲學(xué)思想。
二、蘇格拉底的政治哲學(xué)思想
(一)德性政治本體與知識政治本體的結(jié)合。蘇格拉底政治哲學(xué)的本體論是關(guān)于德性政治和知識政治的關(guān)系問題,試圖回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本體意義。所謂“美德”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的德性,將這種政治美德放在公民身上,認為公民要為城邦承擔(dān)義務(wù),履行責(zé)任。這種責(zé)任和義務(wù)要像“牛虻”,時時給當(dāng)下的雅典城邦以刺激,因為雅典城邦已走向衰落,其標志就在于德性的衰敗。知識政治本體,是關(guān)于城邦和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德性的知識。德性本體和知識本體在公民和城邦政治生活中實現(xiàn)統(tǒng)一。
(二)城邦與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雙重主題。城邦與公民是蘇格拉底政治哲學(xué)思想的核心,對這一核心的論述,回答了古典政治哲學(xué)的主題問題。關(guān)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具有整體主義國家觀的傾向,蘇格拉底主張城邦至上,過以正義、節(jié)制等為原則的追求城邦美德的政治生活。在德性城邦與法治城邦的選擇中,蘇格拉底是以純粹的古希臘人崇尚的公共德性為城邦生活的方式。
在關(guān)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方面,蘇格拉底認為公民的生活方式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卷入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追逐名利,正如一部分智者所教授的那樣要熱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學(xué)習(xí)演講和辯論,熱衷戰(zhàn)爭。另一種則是站在社會政治生活的邊緣,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蘇格拉底認為公民需要做一個積極的沉思者,而不是冷漠的,無望的,不承擔(dān)責(zé)任和義務(wù)的旁觀者,要探討人間美德,關(guān)心政治、關(guān)注政治,要成為為城邦之善盡責(zé)任和義務(wù)的好公民。
(三)蘇格拉底的“正義”觀。在蘇格拉底看來,正義就是知識,倫理是政治性的,而政治又是倫理性的。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蘇格拉底將其看作是管理城邦事務(wù)的藝術(shù),正是借助于這種藝術(shù),人們才能成為優(yōu)秀的政治家。正義是合乎法律的規(guī)定,無論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還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要考慮到正義,正義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標準,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質(zhì)。蘇格拉底認為公民必須維護城邦法律的尊嚴,法律如契約,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約,破壞法律就是破壞契約。
正義也在于公民美德的教育,蘇格拉底認為,美德既然就是知識,因此城邦應(yīng)當(dāng)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雖強調(diào)天賦,但并不否定后天教育,認為自己就是一個負有培育美德責(zé)任的教師。他提出,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是極善或極惡的,而是介于善良與邪惡之間,因此絕大多數(shù)人都需要教育和引導(dǎo)。他教育人們成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說:“最幸福的人和達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養(yǎng)成了普通公民具備的善良品質(zhì)的人。這些品質(zhì)就是所謂的節(jié)制和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