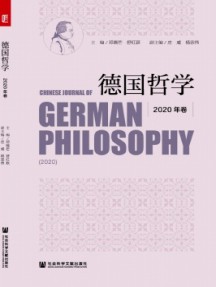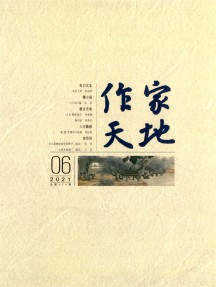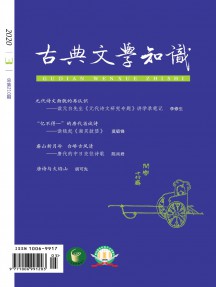古典藝術的特征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4-01-16 10:16:58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典藝術的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古典;藝術;審美;特征
貫穿整個古代史的美學思潮是和諧思想,所謂和諧,就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內容與形式在實踐的基礎上和諧自由的關系。古典主義藝術就是以這種關系為基礎的和諧美的藝術。在和諧美的藝術中,主觀與客觀、再現于表現、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典型與意境、內容與形式、以及形式構成的諸要素,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組成一個均衡、穩定、有序的統一整體。它平穩、舒緩、寧靜,給人的感覺是輕松愉快、毫不費力的,像黑格爾所說,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那樣自由自在。作為一種藝術的類型和美學的表現形態,古典主義藝術的審美特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主體與客體、再現與表現的素樸的和諧統一,要求在表現藝術中有豐富的再現、模擬、寫實的因素,在再現藝術中有濃厚的表現、抒情、寫意的成分,再現與表現水乳般的融合在一起。古希臘詩人摩西尼德斯把繪畫稱為“無聲的詩”,把詩稱為“有聲的畫”。直到文藝復興的達·芬奇還說:“畫是嘴巴啞的詩,詩是眼睛瞎的畫”,本來詩與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詩在語言藝術中是屬于表現、抒情的,畫則是典型的再現,但是在這里詩和畫這兩個概念又超出它狹隘的題材范圍,擴大和上升為深刻的美學范疇。詩相當于表現,畫相當于再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就是表現中有再現,再現中有表現。抒情的詩和模擬的畫在古典和諧美的時代,有一個共同的審美本質,這就是坡說的“詩畫本一律”,也就是再現與表現在古典美的時代所特有的一種素樸的辯證的和諧結合。
二.理想與現實的單一的、素樸的統一。它一方面滿足于現實的理想,不追求現實之外的東西,另一方面又認為具體存在的現實美是不充分的,需要把現實中分散的美挑選出來,集中概括起來,來創造一個兼具眾美的范本式的形象。這樣創造的古典和諧美,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它是現實的,因為它的組成元素都是現實中可以找到的,不迷戀于現實之外的幻想;它是理想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現實事物的美可以符合它,可以達到它。對個體的現實美來說,它是一個理想的范本。
三.情感和理智、想象和思維的和諧統一。客體的再現與理智、思維直接相關,主體表現更多的訴諸情感想象。古典和諧美藝術,再現與表現,主體與客體的和諧,也制約著情感與理智、想象與思維的和諧統一。蘇格拉底即要求“塑造優美的形象”又要求“描繪人的心境”,“表現心理活動和精神方面的特質”,亞里士多德也是既強調模仿和認識,又重視悲劇的情感凈化作用。藝術的再現與表現,與時間和空間緊密相聯。一般的說偏于再現的藝術,側重在空間展開,時間凝練在空間上,時間空間化了;偏于表現的藝術側重于在時間中運動,空間隨時間流轉,空間時間化了,偏于再現的藝術重客觀的物理時空,偏于表現的藝術重主觀的心里時空。古典主義美學由于要求再現與表現的的和諧統一,既重視時間的空間化,又重視空間的時間化,既重視客觀的物理時空,又重視主觀的心理時空,總之,強調時間與空間的均衡和諧。西方古典藝術偏于再現與空間,它以再現、感性、空間為基礎結合表現、理想、時間的因素,它的趣味是把時間空間化,它的時間因素在空間的動勢中暗示出來,它把對象按自然的、感性的、認識的原則來組合結構。
四.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亞里士多德早就強調內容和形式諸因素有機統一的整一美,直至布瓦羅的《詩的藝術》,還在說:“不管寫什么主題,或莊嚴,或諧謔,都要求情理和音韻永遠相互配合”。西方藝術本來是偏于再現 、內容和理智的,從《詩學》的模仿說,到文藝復興的鏡子說,都在不斷的論說這一點,但美在形式和諧的觀念卻是從畢達格拉斯學派,經亞里士多德,直到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的一個傳統的理想,被人稱為形式派的美學。這種本來偏于內容,卻強調形式的現象,正是為了強調內容美和形式美的和諧統一。
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的藝術都鮮明的體現出這種和諧的思想。
古希臘神話包含著豐富的和諧思想。這種思想最鮮明的表現就是宇宙大和諧的思想。人跟自然的和諧是原始人的目的,人跟神的和諧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原始人把想象中的神話世界當作真實的世界,認為自然跟人的和諧與不和諧,都是控制自然的神使然的。人跟神是同源的,存在和諧的基礎,人只有通過對神的信仰和與神的溝通,才可以使神驅使自然為人類服務,形成人、神、物統一的宇宙大和諧。所以,古希臘神話凝聚了人跟自然的理想關系,凝聚了人以和神通神為中介達到跟自然協調統一,形成宇宙和諧格局的理想。這是古希臘神話最為根本的美學意味。
古希臘神話大多綜合的反映了人認識與支配自然與社會的現實與理想。從有關自然與神產生的神話中可以看出,宇宙隨著神的產生而產生,不僅各自有產生的有序性,總體的整一性,相互間還有著嚴密的對應性,反映出原始人對宇宙系統、神普系統及其統一的和諧意識。有關人產生的神話認為,人是普羅米修斯用隱藏著天神種子的泥土捏塑而成,表現了人神同源的思想,表明了希臘人的和諧意識由物的和諧、物神的和諧到神人和諧的邏輯發展。有關神統的神話對應著宇宙物統、社會人統的層次與秩序,表明古希臘人在人神和諧的基礎上,形成了神統、物統、人統完整的宇宙大和諧意識。
篇2
【關鍵詞】《醉了千古愛》 藝術特征
歌曲《醉了千古愛》是由陳道斌作詞,欒凱作曲的一首藝術歌曲。作品一經推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到了廣大歌曲愛好者的歡迎。
歌曲的詞作者是陳道斌,擅長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選取一些非常具有意境的歌詞,結合現代的詩歌語言,創作出具有古典感覺與現代時代音樂相結合的歌詞。所以他的歌詞都非常具有特色,深受歌者與音樂人士的贊賞與喜愛。他的經典代表作品有:《醉了千古愛》、《兵馬俑》、《鹿回頭》。
歌曲的曲作者欒凱,是我國著名的音樂人、作曲者。欒凱從小就開始接受音樂教育,后來他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進行作曲的學習,在作曲系的學習時,欒凱就嘗試進行歌曲的創新,所以從欒凱的音樂作品來看,極具創新精神。他的經典代表作品有:《牡丹亭》、《今夜星光》、《大羽華裳》、《我和祖國》、《千手觀音》等。
這兩位音樂人士合作,創編出了《醉了千古愛》這一首優秀的聲樂作品,帶給人們新的聽覺享受。作品歌詞格調優雅,雍容華貴,意境深遠,精美雅致,曲調優美、婉約動聽,成為民族聲樂教學、演唱和各種聲樂比賽的一首必選曲目。[1]
一、歌曲《醉了千古愛》歌詞格調優雅,雍容華貴
《醉了千古愛》這首歌的歌詞,具有濃郁的古典藝術特征。作詞者陳道斌曾經說過:“一首歌的歌詞就如同散文詩,既具有散文的優美,又具有詩歌的韻味,才能夠創作出朗朗上口的歌詞。” [2]所以在創作《醉了千古愛》這首歌曲的時候,陳道斌就運用了古典與時代相結合的手法,使得歌詞非常的優美,古香古色。其次,《醉了千古愛》這首作品的歌詞是根據音樂旋律所譜寫的,而且歌曲經過了陳道斌的精心設計,使得每一句歌詞都和音樂旋律相互配合,讓人只聽歌詞就能夠感受到音樂之美。除此之外,一些獨特的作詞手法,更是給這首歌曲增色不少。
1.“立象以盡意”手法的運用
在《醉了千古愛》的歌詞中有“巫山”、“滄海”、“天涯”、“春風”、“長亭”、“古道”、“雁”、“梅花引”,這些歌詞都是非常具有古典詩詞特色的,塑造的環境優美悲涼。 而且歌詞中的“巫山”、“滄海”、“天涯”、“春風”,都是用虛詞來進行景物描繪,會讓人聯想到唐代詩人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這句詩。借鑒這首詩詞里面的“滄海”與“巫山”,使得整首歌曲詩意更濃,在美妙的意境之中,讓人沉醉其中。
在歌詞中還有“長亭”、“古道”,與歌曲《送別》對比可以發現,兩者中都有“長亭”、“古道”,而《送別》這首歌曲蘊含了淡淡的送別時的感傷,所以也使得《醉了千古愛》的情感中具有一絲離別之情。
2.“押韻”手法的運用
在《醉了千古愛》中,歌詞書寫采用押韻手法,使得歌曲朗朗上口。每一句歌詞的最后一個字:“外”、“海”、“改”、“哀”、“排”、“猜”、“懷”、“待”、“在”、“愛”,這些字全部的韻腳都在“ai”上面,唱起來郎朗上口,讓人聽過之后,過耳不忘。
二、歌曲《醉了千古愛》曲調優美、婉約動聽
《醉了千古愛》的旋律優美抒情。歌曲為六聲羽(加變宮)調式,是我國傳統的民族小調式,所以整個音樂具有極其濃郁的民族特色。
在歌曲的開始,音樂旋律是以二度級進和三度小跳來進行的,音樂線條較為平穩,如回憶般傾訴。但是在作品的第十五小節開始,音樂旋律從小幅度的起伏開始變為大幅度的起伏,帶動了情感的傳達。而且在第十五小節的小字一組的d和第十六小節小字二組的f,兩個音之間形成了十度音程的大跳,使得音樂旋律忽然出現轉折。將內心的苦悶與掙扎表現的淋漓盡致。
歌曲旋律中還添加了大量的裝飾音,使得音樂旋律在變化中給人帶來不一樣的感覺。倚音與波音的使用,使得音樂旋律非常的生動、活潑,旋律與歌詞結合的更加貼切,增加歌詞的語言性,使得歌曲情感表達更為細膩。
這首歌曲的音域沒有特別寬,作曲者正是借用這些最簡單質樸的東西,向聽眾傳遞最真實感人的情感,使聽眾感受到了聲樂作品中所蘊含的意境。歌曲的曲式結構也并不復雜,相對來說比較簡單,欒凱在為這首作品譜曲的時候,為了使得歌曲能夠便于傳唱,便使用了單二部的曲式結構。整個樂曲一共有九十九個小節,分為AB兩段。在歌曲的兩部分作曲家分別使用了#d羽調式(加變宮) 和e羽調式(加變宮),音樂曲式轉換的同時,采用了類似西方歌劇中由宣敘到詠嘆的方式,營造出了不同的音樂情境,給人不同的音樂感受。
《醉了千古愛》這首新古典民歌作品,在旋律創作上,使用簡單的結構類型進行音樂旋律的譜寫,在簡單中,能夠讓人感受到歌曲的魅力。在歌詞的創作上,運用詩歌與散文的結合,使得歌詞極具古典韻味。詞曲作者對于該曲情感的表達十分真摯激昂,讓聽眾跟隨歌曲感受如泣如訴的愛情。演唱者要對歌曲的情境進行深入的理解,然后結合自己的思想進行藝術的表現。一首成功的音樂作品離不開詞曲作者完美的書寫,更離不開演唱者完美的二度創作。只有演唱者深刻理解作品的內涵,知道詞曲作者所要傳達出來的精神內涵,進而對于歌曲進行細致的演唱分析,才能夠更好的帶給聽眾完美的聽覺盛宴。
【參考文獻】
[1]王升典. 淺談歌曲《醉了千古愛》的創作分析及演唱處理[J]. 通俗歌曲,2015,11:24.
[2]詞作家 陳道斌[J]. 歌曲,2015,06:2.
[3]梁瓊. 欒凱聲樂作品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2015
篇3
關鍵詞:中國古典園林;考察;藝術特點;意義
13年10月份,河北美術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實踐小分隊赴蘇州拙政園及北京頤和園進行了為期20天的實地考察調研。采用對拙政園與頤和園管理處的采訪、對游人的問卷調查等形式重點對于中國古典園林的藝術特點進行深入學習和探索。
1、多種構成要素的完美體現
中國古典園林的構成要素有山石、水體、建筑、植物。
自秦漢就開創了“一池三山”的疊山理水模式。園林理水是中國園林中的一個主題。水在中國藝術,文學,風水中代表相當多的涵義。艮岳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結構最奇巧、以石為主的假山。在傳統園林中,山和水一樣重要,水是流動的,與山的固定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有“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的說法。
明.計成的《園冶》中“掇山”章節包括了池山、溪澗、瀑布等,所以,掇山與理水不可分。
在傳統園林中沿水而置的為各種各樣的建筑,如廳、堂、館、齋、亭、臺、樓、閣、榭、軒舫等,根據其功能分為不同的種類,如廊、橋用于聯系交通、聯結景點,園墻、園窗、園門用于圍護、分割空間。與其他類型建筑相比,園林建筑有著不同于別的建筑類型的特點,如宮殿、寺院等,出自不同的要求或雄偉或嚴肅,一般不追求詩情畫意的意境,但是園林建筑在設計師的創作中就凝聚了很多的內涵,追求含蓄乃與我國詩畫藝術有關,在繪畫中強調“意貴乎遠,境貴乎深”的藝術境界,頤和園的設計就是這樣的,仁壽殿前院由正殿及南北配殿圍成,呈長方形,氣氛較嚴肅,連接仁壽殿與玉瀾堂的夾巷既曲折狹長,又十分封閉,過玉瀾堂前院至西配房,即可透過隔扇窺見昆明湖與玉泉山塔影,出西配房至昆明湖岸,視野突然開闊,昆明湖及西山一帶自然景色全部呈現眼底。
植物是園林藝術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花木猶如山巒之發,水景如果離開花木也沒有美感。植物在園林中有多種功能,本身可構成景色畫面,可以圍合空間,可以陪襯山、水和建筑等各種園林要素,也可以體現寓意,代表了園主的文化背景和個人品格。如拙政園中的聽雨軒,就是建筑與植物完美搭配體現出詩情畫意的例子,聽雨軒的竹、荷、芭蕉完美演繹出“聽雨入秋竹”,“蕉葉半黃荷葉碧,兩家秋雨一家聲”。
2、造園手法耐人尋味
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手法不勝枚舉,一般的園林建筑都不追求巍峨壯觀的仰視效果,但也不排斥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借仰視來加強某些局部景觀的效果,頤和園中的佛香閣,作為大型皇家苑囿的制高點,呈八角多層的樓閣形式,并聳立于重重高臺之上,自下向上仰視,氣勢磅礴,巍峨壯觀。
3、融于自然的空間分割
中國古代園林用種種辦法來分隔空間,其中主要是用建筑來圍蔽和分隔空間。空間分隔力求突破有限空間的局限性,使之融于自然,表現自然。為此,必須處理好形與神、景與情、意與境、虛與實、動與靜、因與借、真與假等關系。
除了用建筑來圍蔽和分隔空間之外,植物用來圍蔽和分隔空間也是很好的。頤和園諧趣園,以游廊連接建筑而形成的界面,盡管繞湖一周而呈閉合的環狀,但畢竟由于湖面過大而建筑的高度又有限,空間感仍嫌不足。為了有效的增強空間感,以參天的喬木進行圍合,在建筑形成的比較密集的界面之上又形成一段較稀疏的界面。
4、南北互融
北方園林以皇家園林為主,規模大,充分利用天然山水,顯現出氣勢宏大的帝王氣概,在色彩處理上主要采用輝煌艷麗的紅黃等顏色。南方園林以私家園林為主,地域有限,顯現私家園林的小巧、活潑,在色彩處理上主要采用淡雅的黑白為主調顏色。南北園林在意境、總體風格、平面布局、空間尺度、色彩處理等方面有著很多的不同,但是這也不妨礙南北園林的互融,將艷麗與淡雅、粗獷與柔美和諧統一。在清代,江南一帶的自然美景成為皇家園林設計的創作藍本,在北方大量運用江南的堆山疊石方法,但是材料以北方的青石為主。如頤和園中的昆明湖就是仿照杭州西湖的蘇堤和“蘇堤六橋”,營造出西提一帶微風垂柳的自然景色。頤和園中的諧趣園仿無錫寄暢園的風格而設計。承德避暑山莊的文人獅子林仿蘇州的獅子林風格設計。
中國古典園林在世界園林發展史上獨樹一幟,是全人類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深浸著中國文化的內蘊,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藝術珍品,是一個民族內在精神品格的生動寫照,是我們今天需要繼承與發展的事業。
參考文獻:
[1]錢海燕:《 中國古典園林的藝術特點及其繼承與發展》,《浙江林學院學報》,2001年第12期。
篇4
關鍵詞:詩詞 數量詞 意象化
詩歌是旋律和意象的藝術,無論寫景敘事,還是章法結構,所有的詩歌元素都極力體現詩歌的意象化特征。數量詞作為詩歌的元素,也必然體現詩歌的意象化特征。
所謂數量詞意象化特征,就是詩人將枯燥的數量詞賦予了意象內涵,將抽象的數量詞極力地具象化,讓數量詞變得有情有義有生命力,把本屬抽象思維范疇的數量運用于形象思維領域,從而獲得奇妙的美學效果和獨特的藝術魅力。
壹:含情脈脈的數量詞
詩歌創作詩歌時,極力地將數量詞進行情感化,實在是神來之筆。
(一)將人生情感人生體驗注入數量詞,使之含情脈脈。如唐代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是妙用數量詞的經典之作。為什么是“兩個”?為什么不是“一個或數個”:“兩個”黃鸝,不多不少,一個就顯得孤寂冷清,多了就顯得雜亂喧囂,唯有“兩個”才可相互鳴叫,一唱一和;唯有兩個才可理解情人間的無限纏綿。
(二)將千年文化內涵注入數量詞中,使之帶有人文情感。如“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中的“六朝”,就是將數詞賦予了朝代更替、世遷的人文情感。從東吳到陳,三百多年間,六個短命的王朝一個接一個地衰敗覆亡,變幻之快,本來就給人以如夢之感;再加上臺城柳的春意盎然與人事滄桑的對照,更加深了 “六朝如夢”的幻境感。一個“六”字就叫人有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的長嘆。
(三)將數量詞進行對比性組合,從而給數量詞注入情感。“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三千”表明了遠離家鄉的過程,“二十”表達了入宮之久的煎熬,“一”、“雙”表明了聲淚俱下,四個數量字全有了動感的主要原因是開成了比對:首先,“三千”、“二十”表多的數詞與“一”、“雙”表少的數詞在詩中兩兩相對,組成對偶句式,“雙淚流”明顯具有動作性,那么“一聲”就有了“唱”的動作,從而賦予了前面的“三千里”“二十年”的動作性;其次,四個數詞形成了虛實對比,“三千里”“二十年”是虛數,“一聲”和“雙淚”是實數,虛數表明故鄉的遙遠、居宮時間的長久,傾訴了她們鄉心漫長和宮怨愁苦。“一”與“雙”是實數,“一”、“雙”兩個數詞,釋放出積蓄已久的悲情,虛實對比,讓數字富有張力,具有鮮明的動作性,因而富于強烈對比的數量詞就成了全詩的靈魂。
(四)將數量詞進行襯托化組合,從而給數量詞注入情感。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千”和“萬”是極言數目之多,創設出宏闊遠大的背景,目的是用“千”“萬”來反襯出“孤舟蓑笠翁”的“獨”,從而表達了詩人凄涼落寞的情懷。
貳:形象生動的數量詞
大師們極善于將抽象的數量詞進行具象化,使之富有意象特征。
(一)將數量詞進行形象化,使之具有意象特征。如范仲淹的《江上漁者》 “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的“一葉”是極有形象性的,落葉飄零,隨風而去,用“一葉”修飾小舟,表現了小舟在狂風巨浪的起起伏伏,象水中的落葉一樣隨波飄蕩。再如秦觀“憶昔西池會,鹓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憶昔西池會,鹓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中的“萬點”表明幽愁之多,用“愁如海”這個比喻來點染,把抽象的萬點愁思具體化、形象化,使之具有意象感。
更為奇絕的是蘇軾妙筆生花的兩個數量詞:《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中的“一蓑煙雨”,生動形象地寫出詩人披著一件蓑衣在風雨中行走,將數量詞轉化為事件,極具意象化。與“蓑笠”、“煙蓑”之類的意象一樣,“一蓑煙雨”從此成為古典詩歌中固定的意象。再如“江上一犁春雨”,春雨只能用“場”來限定。“一犁春雨”更是“皆曲盡形容之妙”,妙就妙捕捉住了雨后春耕的特殊景象。春雨喜降,犁地春耕,作者將農家喜雨,忙于犁地的情形寫得神鬼莫測之妙,“一犁”是寫事件,而用“一犁”來形容“春雨”,將數量詞轉化為意象了。因而“一犁春雨”就成為神來之筆,成了經典中的經典。
(二)將數量詞代詞化,使之具有人的特征。王昌齡的《采蓮曲二首(其二)》“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的“兩”字,既是指荷葉,又是指美女,描繪了荷花似青春少女那樣鮮艷嬌美,而少女的臉龐又如荷花那般紅潤艷麗,人花難辨,融為一體。一個“兩”字既替代了荷花,又暗指了少女,擬人、比喻融為一體,這個兩字就具有了意象性。與“人面桃花相映紅”有異曲同工之妙。
叁:數量詞的時空疊加
大師們創作詩歌時,會將表時間和空間的數量詞進化疊加,同一個數量詞既表時間又表空間,從而具有意象性。如《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數量詞“無邊”“不盡”是全詩的中流砥柱。“無邊”既寫出“落木”的數量,更具有空間感,讓讀者想象出宏大闊遠的空間,讓我們聯想到世世代代人性永遠的秋意;“不盡”寫出了江水之多,有“一江春水”明寫的是空間無窮,更讓我們聯想到數千年來滾滾長江流不盡,人世變遷,朝代更替,長江之水是永遠的,“不盡”具有極強的時間感。“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中的“萬里”,明指萬里空間上的漂泊,是指千百年來無數的人都是“常”“作客”,無家可歸,縱然是回到家,仍然找不到家,仍然是個秋客——詩人明寫自己,何嘗不是寫盡人性的漂泊?從這個意義上說,“萬里”又是個時間意象了。“常”雖然是寫頻率,何嘗不可理解為時間上的“長”啊!“常”和“獨”“萬里”與“百年”兩個數量詞疊加,將時間與空間重疊,將詩人個人情懷與人性的共同點相融合,寫盡了人性的漂泊蒼涼之感。
篇5
關鍵詞:古典芭蕾 “開、繃、直、立” 中國舞蹈 文化藝術
古典芭蕾舞動作的基礎是建立在“開、繃、直、立”的美學基礎之上的,它是一切芭蕾舞動作的基礎,只有符合其美學原則,才能稱得上是完美的古典芭蕾。相比之下,“東方舞蹈的動作都是內向的,腿幾乎總是自然彎曲,并攏;渾圓的雙臂一般都圍繞著身體運動;一切都似乎聚集在一起”。①“開、繃、直、立”是古典芭蕾最為主要的特點,由此對比西方與我國的傳統舞蹈及其他姊妹藝術,便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古典芭蕾“開、繃、直、立”的藝術特征及中西方舞蹈藝術的文化差異。
一、“開、繃、直、立”的藝術特征
“開”――人體動作盡最大的可能向外部拓展。芭蕾舞演員在站立時,腳膝要開成180度,四肢動作要向四面打開。身體從肩、胸、胯、膝、踝5大關節向外打開,最大限度地延長肢體的線條,擴大舞蹈動作的范圍,增強表現力,同時也增強身體的平衡能力和運動的靈活性,使身體理想化、完美化、職業化。
法國舞蹈批評家安德列•萊維森曾說:“芭蕾舞出發點的根本原理――外開性……在一般情況下,人體腿部的動作僅限于前后運動,而當腿外開,就可以使它在任何方向――前、后、旁、斜線、劃圈運動,在所有這些方向,動作都顯得輕松而優雅……”②蘇聯著名編導羅•扎哈洛夫在《舞劇編導手法》一書中表達過這樣的看法:要充分掌握古典舞的全部動作,就必須具有充分外開性的胯骨,這樣才能使雙腳輕松地站成一位,并且令雙腿外開地向前后兩旁抬起。同時,胯部的外開,必然造成舞者收腹、挺胸的直觀效果,強化了身體的直立感。由這種直立感產生的臀部收縮與足部向上踮起,又會給人一種挺拔欲躍的感覺。這樣一來,“開、繃、直、立”在一個基本的站立動作中就得到了統一的體現。由此可見,展開胯部是芭蕾舞訓練中最基本的要求。
舞蹈家以一腿足部為支點,另一腿足面繃直向后盡量高抬、伸展;一臂沿高抬腿伸展的相反方向前伸,形成身體水平方向的直線;另一臂向側后面抬起,與直立的軀干基本成直線,從而產生平衡。此外,人的四肢伸展到了極限,加之腳尖的踮起,強化了縱向的延伸感,使人體在最大限度內向四個方向拓展。
“繃”―― 芭蕾舞種,將膝關節和踝關節繃直,繃起足尖的站立,可謂芭蕾舞最突出的視覺特征,同時,還要求顯示出人體肌肉的外形。
“繃”也是芭蕾舞蹈藝術中非常重要的審美特征之一。芭蕾舞作為一種形體藝術,必須通過“繃”才能將肢體放射到舞臺當中,在有限的空間內使能量聚集在肢體末梢部位,使舞姿更加舒展,從心理上延展了肢體的長度,增強了舞蹈動作的力量感與節奏感。,也拓寬了“開”的審美想象力。
“直”――指雙腿膝蓋伸直以及后背的垂直,也就是使身體垂直拉長,使舞姿舒展優美,達到完美的長線條視覺造型。
芭蕾動作在舞臺中的動作路線也多呈直線形,這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有相似之處,與中國舞的“擰、傾、圓、曲”的審美標準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古典舞蹈中普遍存在的腳腕和手腕的有力回扣,在芭蕾中是見不到的,取而代之的是腳的用力繃直和手的自然伸展。外開的、繃直的腳尖,強化了腿部乃至軀干直立的感覺,加長了人體的延長線,提高了人體重心的位置,造成了舞蹈家向上升騰、放射的效果,也間接地放大了“開”的效果。
“立”――足尖直立,即身體的直立挺拔,使頭頸軀干和四肢作為一個整體,并把身體重心準確地放在兩腿或一條腿的重心上,其空間占有感就像古典宮殿似的傲然挺立,給人以穩定健美之感。
只有在“立”的基礎上,“開”才有條件。穩定健美的“立”是放大延伸的“開”之所以實現的前提。同時,“開”也大大豐富充實了“立”的審美表現力,令“立”不再僅僅是穩定健美的“立”。
由上述可見,作為古典芭蕾動作與美學基礎的“開、繃、直、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雖然我們習慣上經常把它們四者分而論之,但是,從根本上講,它們并非彼此無關或各自獨立,而是共同塑造了古典芭蕾的技術與審美特征。進一步說,“開、繃、直、立”四者中,“開”字為先,“開、繃、直、立”的后三者無不與“開”字相關,無不為“開”字服務,無不受“開”的統攝,在此基礎之上,加之“繃”“直”“立”三者的共同塑造,芭蕾技術與形式美感的大“開”,才更為鮮明地躍然眼前。
二、“開、繃、直、立”與中西方藝術
“開、繃、直、立”的身體造型與西方藝術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雕塑、建筑造型所體現的凸起、清晰的幾何造型觀念相通,而幾何觀念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的各門藝術。
西方音樂中復調音樂的對位法基本構成于幾何原理之上,并使五線譜坐標空間形成多聲幾何主體造型的藝術空間,這正好和芭蕾舞身體強調精確的幾何造型觀念相通。西方的弓弦演奏,下弓常常提得很開,不像中國弦樂(如二胡)的弓夾在兩根弦之間。小提琴的弦張得直直的,加上有指板在弦下面,弦受壓力后不可能像二胡那樣出現彎曲。此外,小提琴等弦樂器演奏時,每個音的手指站位都要求立直,不許拖泥帶水,滑音也不是其基本音樂語匯。這些演奏方面的“開、繃、直、立”給人一種剛勁、剛性的力量。與之相比,中國音樂演奏中的“擰、傾、圓、曲”則給人一種柔韌的感覺。
“開、繃、直、立”呈現外拓性的特點,也體現在歐洲的建筑、園林之中。西方建筑明窗洞開,舉柱偉立,文飾縱橫,并附以精美的雕刻,仿佛要將天下之美盡現于世人目前。宗教中的“神”,要用直觀、崇高、神秘的視覺形式去吸引人們、威懾人們。宗教建筑表現出外向的、放射的形態特征。德國烏爾姆教堂、科倫大教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等,都有又尖又高、鱗次櫛比的塔群,瘦骨嶙峋、垂直聳立的束柱與筋節畢現的飛拱尖券,創造出飛舞之勢。仿佛能使這些巨大的石頭建筑隨時脫離地面,沖天而起,人們的靈魂也隨之升騰,一直升到蒼穹,升到天國上帝的腳下。
西方建筑與園林的這些典型特征在中國古代的建筑與園林藝術中幾乎看不到。中國古代的建筑與園林往往融為一體,共同營造著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然與生命,表現宇宙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元氣流動的韻律與和諧。人與自然的交融合一,不是外顯,也不是外拓,而是強調人與自然的交融,人的主觀心靈與天地自然的溝通,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建筑所強調的營造一種升騰感與神秘感。
由上述可見,中西方藝術不僅僅在技術特征上存在諸多不同之處,在各自藝術的創作與審美理想的追求上都存在著明確而深刻的個性差異。
三、古典芭蕾與中國傳統舞蹈的文化差異
在上文中,探討了中西方舞蹈及相關文化具有的眾多的差異,那么,這些差異源于何時又來于何處呢?
首先,這種差異源于人類文明起源之初,并且可以從中西方不同的語言文字中找到論據。
中國古代甲骨文、鐘鼎文文中的“舞”字寫作
從上圖中的 “舞”字可以看出:其一,“舞”指人體動態。其二,記號著重表現上肢,可見古人“舞”的概念重在上肢運動。其三,記號反映人持物而動,和祭祀、宗教活動有關。
“蹈”字,《說文解字》將其解釋為“踐”的意思,就是以腳踏地。在古代論舞文字中,“舞”往往單獨出現。很少出現把“舞”和“蹈”放在一起連用(即寫作“舞蹈”)的文論。比如現在常用的一個詞――“手舞足蹈”,其中的“舞”和“蹈”分別指上肢和下肢的運動。
在西方,人們將“舞蹈”稱為“ballet”和“dance”。“ballet”源于意大利語,是“跳躍”的意思,而“dance”源于古代高地日爾曼語“danson”,是“伸展”的意思。
從上述對中西方“舞蹈”一詞的語言文字研究中,可以看出:第一,中國人的“舞”著重指上肢運動,西方人的“舞”偏重于下肢運動。第二,中國人注重持物而舞,動作呈弧線或圓形。第三,對于下肢,中國人重視“踐”,即以足踏地,而西方人重視的是跳躍,注重人體擺脫大地的努力。前者是向大地收斂,腳踏實地,與大地相親相依,后者則是向空間開放,意在升騰。③
之所以中國人執著于大地,首先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以農立國,中國人安土重遷,固守大地。中國的建筑一般不向高處發展,而向大地橫向、水平地延伸,例如長城就是典型的中國建筑,是一條盤旋在中國大地上的長龍。中國的四合院也是在平面延伸,不向高空發展,即便是故宮中也幾乎沒有什么樓房。所謂的“黃鶴樓”、“岳陽樓”、“鸛雀樓”等,其實都不是很高的建筑。中國人登高只是望遠,看的還是平面大地而已。偶然想象升空,最后還是想回到大地:“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其次,古典芭蕾的“開”可以從舞蹈動作中找到例證。
在芭蕾舞的動作中,跳躍動作的種類眾多,出現頻繁,有中跳、小跳、大跳等。每種跳又分成不同的類型。比如,小跳有擦地雙落跳、擦地單落跳、滑步、雙起單落跳等;中跳有帶跳的空中單腿劃圈、敞式西松、閉合式西松等;大跳有凌空越或大跳、變身跳等。大幅度的跳躍是造成芭蕾舞中人體向空間拓展形態的重要原因。④然而,在中國古典舞中,跳的動作不但少,而且相對于芭蕾中的跳,其跳的幅度和高度都小。
從芭蕾舞多騰跳動作,而中國舞蹈缺少騰越動作這一點看來,也可以說明另外一個問題,即西方的舞蹈講究通過外部的形體與造型,表達外在的宏大與延展,中國傳統舞蹈則更為講究舞蹈動作與造型的內在氣韻。
對上述觀點,有人認為,以古典芭蕾為代表的西方舞是為了使人從大地解放,以確證自己的存在,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張揚,因此偏重于下肢的動作。芭蕾舞往往要掂起腳尖,高跳、蹦腳,具有放射性,仿佛要擺脫大地的懷抱,尋找新的空間,試圖通過不停的跳躍,飛上天空,尋找自由。然而,東方舞則很少有腿部的彈跳動作,表現的是對大地的眷戀,總是依依不舍地在大地上徘徊,因而偏重上肢的運動。這恰與《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表達的看法不謀而合:西方的舞蹈者總是試圖使自己擺脫地心的吸引力,努力跳起來,在空中翱翔。中國、日本和朝鮮的舞蹈者則牢牢站在地面上,很少把腳高抬,他們沿著一定的幾何形,緩緩地移動腳步;臂和手的動作千變萬化,而且極受重視。而在西方舞蹈中,很少應用手的動作。這又如法國的瓦萊里的觀點,即“舞蹈是為了從大地獲得解放,是為了確認自己的存在”。⑤日本舞蹈評論家郡司正勝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日本舞蹈所表現的是眷戀大地,是依依不舍地在大地上往來慢行……西方舞蹈是放射性的,是憧憬天上;東方舞蹈的動作是內涵的,是眷戀大地的……日本舞蹈所要表現的,并不是要離開生活尋找具有新的時間和空間的美的另外的世界,倒是以大地為樂土”。⑥
綜上所述,古典芭蕾的“開、繃、直、立”并非偶然而就,其形式與審美特征不同于中國傳統舞蹈,離不開其自身的文化,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差異,從根本上講,都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與民族心理、性格所造就的。中國人的含蓄,使得中國人所塑造的生活環境與藝術也是含蓄的;西方人天生自由開放,他們所創造的生活環境與藝術也是外拓外向的。
(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注釋:
①安德烈•萊維森:《古典舞蹈精粹》,《舞蹈摘譯》,1984年第2期,轉見《人體文化》,94頁。
②安德烈•萊維森:《古典舞蹈精粹》,《舞蹈摘譯》,1984年第2期,轉見《人體文化》,133頁。
③謝長、葛巖:《人體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31頁。
④謝長、葛巖:《人體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