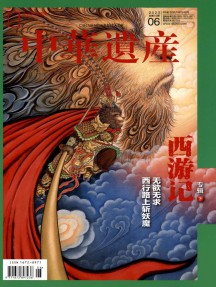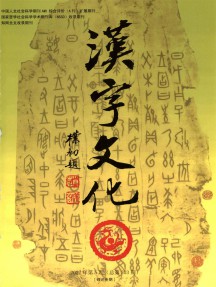漢字與古代文化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12 15:35:46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漢字與古代文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其實,農業的“農”字的古文字字形,正記錄了蚌殼和農業之間的密切關系。農,小篆作“ ”,其對應的楷書寫法作“ ”。《說文》解釋說:“ ,耕也。從辰,囟聲。”其中的“ ”是兩只手的變形,農耕需要用手,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囟”又是什么,就很難從小篆字形中看得出來了。于是,我們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看能否找到答案。
“農”金文作。從這個字形中我們可以發現,原來“ ”中的“囟”并不是聲符,而是“田”的變形。“田”四周有四個“屮”,合起來就是“”,也就是草莽的莽,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樣子。田里長滿野草,要想種莊稼,就需要先把雜草除掉,字形的下面,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樣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與小篆字形對應起來,正是其中的“辰”。那么,“辰”究竟代表一種什么樣的除草工具呢?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釋辱》:“尋辰字龜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實蜃之初字。”楊氏認為辰這種農具就是“蜃”。蜃是一種大蛤蚌,古時候沒有鐵器,農民是用蜃殼來翻土除草的。這在《淮南子•論篇》中有記載:“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誘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龍山文化都出土發現了蚌制的鐮。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多為河流沖積的黃土地帶,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使用不太堅硬的工具,就可以進行耕作,這是石制和蚌制農具在當時得以廣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時期,石、蚌類農具仍大量使用。這時的蚌制農具已有“蚌耜”、“蚌鏟”、“蚌刀”、“蚌鐮”等。前二者是整地農具,后二者是收割農具。
“辰”和“囟”的來歷搞清楚了,“ ”字的構形問題就好解釋了。把田、、辰三個部分結合起來理解,就可以得出這個字的本義:兩手持蜃殼除去田里的雜草叫農。遠古之時,森林遍布,在耕種播種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樹木,清除野草,沒有金屬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殼來作為生產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銳之蜃殼以鏟除雜草,翻松土壤,以便種植莊稼。故《漢書•食貨志上》說:“辟土殖谷曰農。”(辟:開墾)
還有幾個字與“農”關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說文》說:“ ,早、爽也。從從辰。辰,時也。辰亦。”許慎把“ ”當形聲字來解釋,是他沒有真正理解“䢅”的構意。“晨”甲文作、,從辰從二屮,或從二木,與我們前面分析的“農”字構意完全相同。其實,“晨”和“農“本來就是一個字。農是下田除草,古人農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興夜寐”,早晨起來就開始干活了,所以,當時人們就直接拿表示干農活的“農”字來表示早晨。后來“晨”字才逐漸從“農”字中分化出來,先寫作“ ”,從從辰,表示雙手持蜃,其構意與“農”字仍無區別;后來為了強調早晨的時間意義,就改成從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從辰從寸。寸在漢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從辰從寸的“辱”和從從辰的“ ”,在構意上也就沒有區別了。這說明,“辱”字同樣是從“農”字分化出來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動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頭作“蓐”(用“辱”字表示恥辱是假借的用法)。后來出現了木制的除草農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來出現了金屬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寫作“”。《說文•木部》:“,薅器也。從木,辱聲。,或從金。”
“”字還有一種從“耒”的寫法,即“耨”。《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耨,所以來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據“柄長一尺,刃廣六寸”可知,是一種很短的除草工具,人們使用時的姿勢與持蜃并沒有太大區別。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寫作“耨”,是因為“耒”字本身就是一種農具。如果說蚌制農具是我國最早的生產工具之一的話,耒則是在傳統農業中最為重要、使用歷史最長的一種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隨火耕的需要而來的,火耕是一種比較古老的大規模的耕作方法。對于火耕而言,漫撒和點種是兩種主要的播種方法。點種的主要工具就是尖頭木棒。但是尖頭木棒畢竟效率不高,先民為了滿足增產的要求,在原始農具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改造了尖頭木棒,形成了一種新的農業工具。這種新農具把尖頭木棒延長,長到可以立著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時在它的下部,距離尖端不遠的地方,添加上一個短小的橫木,用它作為踏腳,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這樣,人們勞作時就省力多了。這種改造了的原始農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見的除蜃之外的主要發土工具。《說文解字》說:“耒,手耕曲木也,從木從豐。”金文“耒”字形作或,從形體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種帶有兩個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彎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彎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獨體象形字,從形體上看,是一種曲木棍上綁著踏腳橫木的單齒發土農具。許慎《說文解字》說:“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災。”這是說“力”的本義是人體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義。許慎的說法并非“力”的本義。徐中舒曾明確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從力之字,有時也從耒。如“男”字,《說文》說:“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確實是從田從力,不過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這種農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這種農具耕田的樣子。金文中“男”字還可以寫作,, ,“田”下的形體由“力”變成了“耒”。可見,“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體比較接近,只是“力”下面沒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談到“耒”,就不能不說一下“耜”,因為古書中“耒耜”經常連用。從“耜”字從耒這一點,便可以看出二者間的密切關系。耒耜同為起土的工具,耜的形狀和今天的鏟比較相似,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辭》是最早記載古人發明耒耜的文獻:“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從“斫”和“揉”兩種制作方法上,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而“耜”則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為耒”就是用火將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適的彎曲度;“木為耜”較耒復雜,需要將整段木材劈削成圓棍形的柄和鏟狀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種的主要農具,二者連起來常用作各種農具的泛稱。因此人們在為其他農具,特別是木制或裝有木把的農具造字時,常常以耒為構字部件,如“耙”、“”、“”等。
篇2
“火”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種寫法,如、、等,都是像火焰之形的象形字,其上的點畫像火星飛濺的樣子。火的顏色為“赤”,“赤”字甲骨文作、、等形,小篆作,從大、火會意,大火之色即為赤色。《尚書•洪范》:“火者,赤色也。”在商代卜辭中,“赤”字也多表示火的顏色。也有學者認為,赤字從大從火,其中的“大”并不是大小的“大”的意思,而是像大人之形,從大從火是表示用火來燒人,這可能是當時的一種刑罰,或者是當時的一種祭祀儀式。《摭續•二九一》中說“貞,勿赤”,赤用為動詞,很可能是焚人以祭祀的意思。《鐵•一•二》:“癸卯卜,貞,又赤馬……”所謂赤馬,則可能是焚馬以祭祀之義。
與大火相對的是微火,微火最初用“幽”字表示。“幽”甲骨文作、、、等形,從火從會意,其中即絲字,絲線的特點是比較細微,故從火從正可以表示微火之義。引申為凡微小之稱。《爾雅•釋詁》:“幽,微也。”如今杭州等地仍將微火叫作幽,這是古代漢語在現代方言中的遺留。由于甲骨文中“山”和“火”形體相近,經常發生混同,所以后來“幽”字就變成從山了。《說文解字》中小篆的“幽”字作,從山從,這其實是從火從的訛誤。
《管子•輕重》記載:“炎帝作,鉆燧生火,以熟葷腥,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學會用火加工食物,是人類生活方式的一大進步。如“炙”字,小篆作,《說文解字》云:“炮肉也。從肉在火上。”所謂“炮肉”,就是以火烤肉。籀文作,添加了一個表示肉串的偏旁,進一步說明了“炙”的具體方法,是將切割好的肉塊用東西串起來進行燒烤。《詩經•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毛傳曰:“炕火曰炙。”孔疏:“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這些釋義正可與《說文解字》籀文相印證。火烤是人們最早掌握的加工食物的方法,后來隨著陶器的發明,人們才知道燃火于器皿之下,用沸水來煮熟食物。例如“爨”字的構形,正反映了燒火煮食的形象。“爨”字小篆作,上像兩手持釜甑等灶具之形,中間“冂”像灶門,下像兩手持木柴添入火中,幾個部件組合在一起,正是一幅燒火做飯的畫面。
除了用來熟食,火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照明。如“叟”,現在作老叟講,但其最初的意思是搜尋。“叟”字小篆寫作,甲骨文作,上像屋舍,下像一只手高舉火把,組合起來正是手持火把在屋中搜尋的形象。隸楷之后,“叟”的形體發生訛變,全然看不出本來的意思了。據《方言》記載,戰國時代齊、魯、衛等國將老人稱作叟,《說文解字》也說“叟,老也”,可見“叟”作老叟講也是很早就出現了。為了區分搜尋和老叟這兩個意義,人們便在表示搜尋義時增添了提手旁,寫作“搜”。
火在古代田獵活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原始圍獵的主要方法就是焚田。所謂“焚田”,就是以火燒毀叢林草木,使百獸無處隱匿,最終被火圍困在中央,便于集中捕殺。《爾雅•釋天》:“火田為狩。”郭注:“放火燒草獵亦為狩。”“焚”甲骨文作、、、、、等形,從火從林,或從火從,或從火從木,像以火燒草木之形。古文字中從與從林、從木意義往往無別。甲骨文“焚”字還可以寫作,這是較為復雜的寫法,下面增添了秉持火炬的一雙手,但整個字的構意并沒有發生變化。商代卜辭中,提到“焚”的時候都是指的田獵之事,這可能是由于上古時代草莽叢生,禽獸繁衍,所以卜辭屢見焚田的記述。如《甲骨文合集》10198片:“翌戊午焚,禽(擒)?”意思是說,第二天以燒山林的方式打獵,能夠擒獲野獸嗎?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不少焚田圍獵活動的記載。如《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孟子•滕文公》:“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可見,這種圍獵方式在古代十分常見。但是,焚田而獵的方式有似于竭澤而漁,不利于動物的繁衍,是一種短視的行為。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這樣做的危害,如《韓非子•難一》:“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后必無獸。”但在遠古那種生存環境中,人們的這種做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左傳•成公十三年》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和戰爭是國家最重要的兩件大事,火在這兩件大事中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字,小篆作。《說文》:“,柴祭天也。從火從。,古文字。祭天所以也。”“”字甲骨文作、、、等形,像木柴架在火上燃燒的樣子,周圍的點畫象征四濺的火星;下面有的加“火”,有的不加“火”,這只是形體繁簡的不同,構意上并沒有多大差別。《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邢疏:“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說的就是燒柴以祭天的儀式。《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高誘注:“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于上而燎之,升其煙氣。”燎祭就是將玉帛、牲畜置于燃燒的薪柴之上,用產生的煙氣上達于天來祭天的儀式。這里的“燎”就是“”字。“”字形里本來是有“火”的,但由于字形的訛變,其中的“火”看不出來了,為了強調“”與火有關,人們就在“”的形體上又添加了一個“火”,這是漢字頑強地堅持表意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其實,在小篆形體中,“”就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變形,看不出木柴燃燒的形象了,許慎根據小篆字形所做的解釋并不符合“”字的最初構造意圖。
火在戰事之中也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例如《說文》火部:“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意思是說,烽火和燧一樣,都是古代望敵情用以報警的信號。在交通極不發達、通訊手段極其有限的古代,一旦邊關告急,人們靠什么來快速傳遞信息呢?火便是當時最佳的選擇,無論是白天或夜晚,火都可以靠其光亮和濃煙,將信號迅速傳至遠處。《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說的正是以烽火來調遣軍隊的事。用烽火調動軍隊,是關系國家安穩的很嚴肅的大事,但是周幽王卻為了博得妃子一笑,竟然用烽火戲弄諸侯,最終招致國滅身亡,為天下人恥笑。周幽王是西周時期最后一個君主,是個荒無道的昏君。周幽王貪愛美色,鄰國投其所好,為他選送一個名叫褒姒的絕色美女。幽王雖然對褒姒百般寵幸,但褒姒卻面若冰霜,始終不肯啟齒一笑。幽王為此十分煩惱。有個叫虢石父的佞臣,替幽王想了一個主意,提議用烽火臺一試,幽王不顧國家安危,竟然答應了。他帶著褒姒登上驪山烽火臺,命令守兵點燃烽火。一時間,狼煙四起,烽火沖天,各地諸侯一見警報,以為京城告急,急忙帶領本部兵馬急速趕來救駕。到了驪山腳下,卻見幽王和褒姒高坐臺上,飲酒作樂,諸侯們才知道是被戲弄了,紛紛懷怨而回。褒姒見千軍萬馬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如同兒戲一般,覺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嫣然一笑。幽王見狀大喜,立刻重賞虢石父。結果,等到后來犬戎真的打過來時,幽王再命令點燃烽火,諸侯們因上次受了愚弄,這次害怕再被愚弄,就都不理會了。幽王最終被敵兵亂刀砍死,西周也因此而亡。
篇3
不同地區的文明在起源于水邊這一點上是相似的,而不同民族對“水”的認識卻可能存在差異。水字在甲骨文中寫作,像水從高處順流而下之形。而古埃及文字中的“水”則寫作,像水面波紋之形。這兩種古老的文字在造“水”字時,同樣地直接取象于水的形態,然而卻一為豎,一為橫。甲骨文之“水”是順勢而流,描繪的是水的流動之貌;古埃及之“水”是平面的水紋,描繪的是靜止的水面。我們可以從這兩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地貌來尋求原因。我們知道,中國與埃及的地勢是不同的,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江河發源于西部的高原和山區,順著地勢向東而流,先民們首先觀察到的是“不廢江河萬古流”,于是取水的流動之態而造“水”字。尼羅河發源于非洲中部,流入埃及后已經是下游,所以埃及地勢開闊平坦,支流呈發射狀,而非朝一個方向流淌,水面也相對平靜,于是以微波蕩漾的水面來造“水”字。由于地貌的差異,形成了同樣是象形的“水”字,一為豎的流動狀,一為橫的靜止狀。另一方面,漢字字形在某種程度上受漢民族思維習慣的影響。在古人觀念中,水沿著河道流淌才是常態,而水橫流則是水災。
水順著河道而流,可以灌溉天地,為民謀利,故為“水利”。《說文》中有(即“畎”字)、(即“澮”字)、川三字,小篆分別作,,,皆像水順流之貌,是上古時期的農田水利設施。從形體可以看出,它們的區別是水流大小不同。《說文?部》:“,水小流也。”小篆像一彎小小的水流的樣子,表示田間小的排水溝或引水渠。《說文?部》:“,水流澮澮也。”“澮”從水會聲,“會”同時也表義,表示會合水流之義,所以“”就是由小水流匯合而成的較大的排灌渠。“川”字在甲骨文中寫作、、等形,其構意均像兩岸間有流水,故指流通的水。農業文明興起后,引河水灌溉農田,“川”便成了農田水利設施。《說文?川部》釋“川”曰:“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距川。言深之水會為川也。”大意是說,把和等水流深挖疏通,使它們匯集在一起,就成了“川”。《周禮?考工記?匠人》把田間的灌溉渠, 按其大小和所在位置的不同,分為、遂、溝、洫、,最后由匯集成川。可見,在整個排灌系統中,“”最小,“川”最大,中間依次有遂、溝、洫、,一共六級,水利設施非常完善。這說明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很早就認識到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目前已發現距今6000多年的原始水田遺址及其排溉設施,如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的浙江吳興邱城遺址中發現了大小不同的排水溝和引水渠。《詩經》中也有引水灌田的詩句,《小雅?白華》載:“池北流,浸彼稻田”,講的就是用池的水來灌溉稻田。
水橫流則為水害。漢字古文字中也有像古埃及“水”字類似的形體,但卻是用來表示大水泛濫成災。甲骨文中有、等形,皆是大水橫流之形,表示水不順河道流淌,是水災之“災”的本字,體現了古人“不順”即為“逆”,“逆”即成“災”的觀念。“災”字在甲骨文中還可以寫作,在“川”中加一橫,意為河流中間被堵塞。大水橫流,河道被壅塞,水便不能順流入海,勢必造成大水漫溢,淹沒農田,摧毀村莊,影響人類的生存,可見古人對水患的認識是多么深刻。在世界各大洲的古老民族中幾乎都有關于史前大洪水的傳說。在中國,相傳在遠古時期,上天發大洪水懲罰人類,地面上一片,只有伏羲和女媧兄妹兩人躲在大葫蘆里才幸免于難,成為華夏民族的始祖。在西方,則有諾亞帶著家人登上方舟躲避洪水的故事。在蘇美爾、印第安等許多古老民族中都有這樣的神話傳說,因此,有學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始于大洪水傳說。
在洪水侵襲時,古人并不是束手待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與洪水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流傳著很多治水的故事。在中國,最為廣泛傳頌的治水英雄就是大禹。上古堯帝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莊稼被淹了,房子被毀了。堯先派鯀去治水,鯀花了九年時間,采用“堵”的方法,沒有把洪水制服,被處死了。堯又派鯀的兒子禹去繼續治洪水,禹吸取父親的教訓,采用開通淤積、疏浚河流的方法,帶領群眾鑿開了龍門,挖通了九條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禹八年于外,三過家門而不入,終于平息了洪水。“疏浚”的“浚”又寫作“”,其古文字字形正反映了古人疏導河流的治水方法。“”,甲骨文寫作、、,從從或,像剔去筋肉后的殘骨,旁邊的小點是剔下來的肉屑,或是坎。小篆寫作,“”省去了旁邊的小點并整齊化,坎變成了“谷”字,《說文》釋為:“深通川也。從谷。,殘也;谷,坎意也。”其中的 由殘骨而表示殘穿、鑿穿,“深通川”就是要用鑿穿山谷、深挖隧道的方式疏通水流。這正是《尚書?禹貢》所記載的大禹治水的方法:“禹別九州,隨山川。”意思是說禹劃定中國國土為九州,并順著山勢開鑿水道,疏通水流。
雖然古文字的“水”取象于水流動形,但古人對靜止的水也有細致的觀察。靜止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所以在青銅鏡產生之前,古人就用一盆水來充當鏡子。甲骨文中有幾個形體:、、,構意均是一個人俯身對著一盆水照自己的臉。這幾個形體就是后來的“監”字,本義為以水照容貌。后來發明了銅鏡,便在“監”旁加一義符“金”,寫作“”字,現在又簡化為“鑒”。《莊子?德充符》所說的“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正是用的“鑒”的本義,意思是說沒有人用流動的水來照影,而是用靜止的水來照。水能忠實地反映人的美丑,這個特點被應用到政治上,就有了《尚書?酒誥》中的名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這是以用水照影打比方,說明一條抽象的政治哲理:黎民百姓就像水一樣能照出統治者的形象,統治者應該以黎民百姓為鏡子來照出自己的政德。
篇4
“陶”是形聲字,義符是阝,阝是“阜”字作偏旁時的省變,從“阜”的字意義都跟高地有關。那么,陶器的“陶”字怎么會與高地有關系呢?《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從阜聲。《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所謂“再成丘”,按照三國時期孫炎的說法,是“形如累兩盂”的土丘,也就是像兩個摞在一起的用土燒制的陶器盂一樣,當地因丘而得名,所以地名叫陶丘。這個地方漢代屬于濟陰郡,大致在現在山東的定陶附近。據說堯最初曾被封于陶丘,后來又遷到唐地,所以才稱為陶唐氏。也正因為如此,堯的子孫后來才有的以陶為姓,有的以唐為姓。姓陶的祖先還有另外一支,那就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虞閼在周朝時做了“陶正”的官,也就是專管制作陶器之事的官,后來虞閼的子孫就以官為姓,也姓陶。《姓纂》上解釋陶姓的來源時說:“陶唐氏之后因氏焉。虞閼為周陶正,亦為陶。”很簡要地概括了兩支陶姓的來歷。可見,“陶”字之所以可以表示高地、地名以及姓氏,都跟陶器有著密切的關系。
其實,陶器的“陶”是因為用來表示陶丘才加上了“阝”字旁,原來表示陶器的字只寫作“”。“”字金文作、,右上方像一個彎腰的人形,中間部分表示工具杵,最下面像一器皿,整個字形像一個人持杵在器皿中搗東西。具體是搗什么呢?《老子》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其之用。”《荀子•性惡篇》也說:“故陶人埏埴而為器。”唐代楊注解說:“埏,擊也;埴,粘土也。擊粘土而成器。”通過搗擊粘土而制作陶器,這正符合“”字的金文構形。原來,“”字中的那個人,是在拿著杵在器皿里搗粘土呢!這是制作陶器必需的程序。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就學會將具有黏性的土壤搗碎,用水調和,利用土的可塑性塑成各種器物。所選的粘土也是非常講究的,《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只有這種細膩的黃土,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
《說文》對“”字是這樣解釋的:“,瓦器也。從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案:《史篇》讀與缶同。”所謂“瓦器”,是一切用土燒制的器具的總稱,這一點我們在以前講“弄瓦之喜”時已經說過。而說“”的結構是“從缶,包省聲”,這是許慎沒有見到過“”的金文寫法的緣故,他把“”字中人形解釋為“包”字的省簡,這是一種誤解。許慎說“古者昆吾作”,是對古代傳說的記述。昆吾是夏商之際的一個部族,據說是顓頊的后裔吳回的后代,吳回在帝嚳時期成為了南方的部落首領,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即專門掌管火的官員。昆吾掌管火,他的后明燒制陶器的技術,這應該是合乎情理的。許慎還引用《史篇》說,“讀與缶同”,這正點明了“”字與“缶”字的密切關系。“缶”甲骨文作磐,如果再在右上邊加上“人”形,就成了金文的“”字了,可見,“”“缶”二字實同出一源,都是表示搗土制陶之義。所以《說文》對于“缶”的解釋也是“瓦器”。
缶作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多用來盛酒漿、糧食或其他小件的東西,當然也包括一些貴重的寶物。所以寶貝的“寶”字中原來就有個部件“缶”。“寶”繁體字作“”,金文作、等,從宀從貝從玉從缶,表示把貝、玉這些寶物儲藏在缶中,放在房子里藏起來,由此會合出“寶”字含義。由于“寶”與“缶”古音相近,所以也有學者把“缶”理解為“”字的聲符。
缶除了作日常儲物的容器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功用,那就是充當打擊樂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樂。”李斯《諫逐客書》:“夫擊甕叩缶……真秦之聲也。”這些記述說明,甕、缶、瓴之類的陶器具古代經常被用作樂器。受缶類陶器可以充當打擊樂器的啟發,先民創造了許多形態各異的陶制樂器,如陶塤、陶鼓、陶鈴、陶鐘、陶角、陶響球等樂器,演奏方法有吹奏、有擊奏、有搖奏。在西周初年,人們依據制作材料將樂器分作八類,即:金、石、土、草、絲、木、匏、竹。這就是所謂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樂器,可見陶器在先秦時期的音樂生活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厚薄不均。隨著制陶技術的發展,原始社會末期出現了陶均。陶均是一種水平固定在短軸上的木質圓盤,人們將陶坯放在旋轉的陶均上,在緩慢轉動中逐漸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勻。“均”字從土勻聲,它其實是由“勻”孳乳而來的,與“勻”的意義有著密切的關系。關于“勻”的古文字構形,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解釋。我們認為,甲骨文中被人們釋作“旬”字的、、等形,就應該是“勻”字,其構形正像將捶打好的泥片旋轉著置于陶均之上,其中的一個短的筆道,像用木鏟之類的工具將多余的泥片切掉。這樣的工具在制陶過程中是很常用的(如圖)。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細膩勻稱,所以“勻”就引申出均勻的意義,為了與均勻的意義相區別,表示陶均時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轉圈的,這正與古代表示時間以十天為周期循環往復的情形相似,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勻”表示十天,后來又增加“日”旁作,這樣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勻”、“均”、“旬”三字屬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須用高溫才能燒制成功。在制陶的過程中,先民逐漸認識了各種原料在高溫燒制下發生的形態變化,當他們嘗試用高溫燒制金屬礦物時,冶金業也就慢慢出現了。可以說制陶技術的發展為金屬的冶煉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溫燒制,所以后來二者組合成一個雙音詞“陶冶”,比喻在困境中磨練培養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說文》解釋作“銷也,從臺聲”。,是古“冰”字。許慎認為冶煉金屬就像融冰一樣,所以用“從”釋“冶”。但是,考察“冶”的早期字形,并不從“”。戰國文字中“冶”的較典型的寫法作,從刀從火從口從二。從火很好理解,從刀(或從刃、從斤)表示冶煉而成的器具,而從口從二則眾說不一。不少人認為,“口”“二”是羨符,也就是多余的沒有實際意義的筆畫。不過,聯系“金”字的構形,將“二”理解為羨符的說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屬的總名,并不專指黃金,常見的有所謂的“五色金”,即黃金(金)、白金(銀)、青金(鉛)、赤金(銅)、黑金(鐵)。“金”字金文寫作等形,人們對其構形的認識并不一致。但多數人認為字中的兩點或三點像金屬餅塊或礦石之形,右側下面是“土”字,表示金生自土中,上面的即是“今”字,充當聲符。在西周銘文中,“金”有時就寫作,足以證明這些點并非羨符。同時也說明,冶煉的“冶”字中的“二”,既不是冰,也不是羨符,而是用來冶煉金屬器具的金屬餅塊或礦石。
“礦”字的古文作。段玉裁解釋為“在石與銅鐵之間,可為銅鐵而未為成者也”,也就是礦石。字的構形應該是模仿礦井的形象。據《周禮》記載,當時就已經有“人”這樣的官職,專門掌管金玉錫石之地,甚至在殷商卜辭中就已經出現視鑿金于山為國之大政的描述。這說明,礦石的開采和管理很早就受到官方的重視。
冶煉金屬的目的就是要鑄造各種各樣的金屬器械。“鑄”字《說文》解釋為“銷金也”。甲骨文和金文作、等形,上面像兩手掬著鑄器,下面為器皿,器皿內有火。也有人認為前一形體像手持器具將金屬液傾倒入器皿之中,這個器皿就是鑄造器具的模型,也就是所說的“范”,“模范”二字連起來可以指典型和榜樣,就是從鑄造器具引申而來的。“鑄”字后來到睡虎地秦簡時變成了,由金、火、壽三個部件組成,前兩個部件表意,后一個部件表音,整個字變成了形聲字。再后來,部件“火”省去,就成了現在的左金右壽的“鑄”字了。
篇5
飲食進入文化的范疇,要從熟食開始。燧人氏鉆木取火的傳說已經在考古資料中得到了印證。自從學會用火之后,人類才告別了“茹毛飲血”的蠻荒時期,從而真正步入文明時代。因此,火促進了人類飲食習慣的重大變革,也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重要發展。《禮記》在追溯人類與火的歷史時說:“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鄭玄注:“炮,裹燒之也;燔,加火上;烹,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這里所說的炮、燔、烹、炙,是當時用火加工食物的四種方式,它們的不同特點大致可以從其字形結構中得到反映。
“炮”字從火包聲,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聲音之外,還表示包裹的意義。鄭玄注所說的“裹燒之”,也就是用泥巴包裹著食物放進火里去燒,這種加工食物的方式類似于現在的“叫花雞”。關于叫花雞,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古時候江蘇常熟有個叫花子,有一天很幸運討了一只雞,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來分享,便將整只雞連毛用荷葉包裹好,再涂上泥巴偽裝起來,胡亂塞入火堆里燒烤,等別的叫花子都不在時,他趕忙把雞從火堆里扒出來,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驚喜地發現,燒雞不僅通體金黃,而且味道異常香酥可口,還略帶泥土的芬芳,堪稱是雞中極品,從此以后叫花雞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實,從“炮”的字形以及《禮記》的記載來看,類似叫花雞的做法早在幾千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區別的,但現在我們已經無法考證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從“炙”的字形看,下面是火,上面是“肉”的變形,再結合鄭玄所說的“貫之火上”,可以想見“炙”是將肉串起來,架在火上去烤,估計與現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過,當時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塊,有時候也會把整只動物串起來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種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來沒有下面的部件,只寫作“亨”。甲骨文作,金文作,《說文》作。《說文》所解釋的本義是把煮熟的食物獻給鬼神。其字形有的說是像宗廟之形,有的說像盛滿食物、上面加了蓋兒的器具之形,但各種說法都離不開宗廟祭祀,由此可見熟食與祭祀之間的密切關系。“古之大事,惟祀與戎”,祭祀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當時烹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這么單純,當時除了要供給人們膳食之外,還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禮》有一種官職叫“亨人”,其職責就是在準備祭祀品的時候,專門負責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鍋中水量的多少。《周禮》還有兩種和做飯有關的職務,叫“內饔”和“外饔”,“饔”的意思就是熟食,內饔是掌管宮廷內王、后和世子們的伙食的,外饔是掌管祭祀時設計祭品的。亨人在內饔、外饔的工作中充當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是食物煮得好壞的關鍵。
其實,不僅“烹”、“亨”二字本來是一個字,還有享受的“享”,也與“烹”字屬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為一形,后來才逐漸分化成三個意義密切相關的字。煮食物的意義專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供奉給宗廟上的鬼神,誠意通達于鬼神,這樣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聞到祭品的馨香,便欣然享用,這樣便有了“享”字。直到現在,方言里還有將這幾個字混用的情況,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區稱用鐵鍋燒水為“享水”,用瓦罐把茶燒開叫“享茶”。通過“烹”、“享”、“亨”幾個字之間的淵源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烹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飲食與祭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烹”字現在與“飪”連用,構成一個雙音詞,泛指做飯做菜。但在古代漢語中“烹”、“飪”很少連用,即使連用,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而飪則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說文》:“飪,大熟也。從食,壬聲。”《論語•鄉黨》:“失飪不食。”何晏注釋說: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也就是說,煮食物必須熟度剛好,既不能半生不熟,也不能過于熟爛,這樣才符合禮儀的要求。特別是祭祀的時候,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標準,是絕對不能用作祭品的,否則就是對鬼神的不敬。“烹”“飪”二字連用,最早見于《周易》:“鼎,象也,以木翼火,烹飪也。”這里的“烹飪”雖然連用,但還沒有成為一個雙音詞,其中“烹”表示煮的過程,“飪”表示煮的結果。“烹”、“飪”相連,構成了食物原料由生變熟的一個完整的加工過程,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發展到烹煮的熟食法,再到講究食物生熟度的進程。
“烹飪”是對食物進行加工處理的過程,“飲食”則是對“烹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詞和動詞兩種意義,既可以指吃的動作,又可以指吃的對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對象都可以叫食,最初食是專指主食,“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來的事。“食”字甲骨文作“”,一般認為像一個盛食物的器具,上面像器具的蓋子,下面是盛食物的圓形器具。這種圓形的盛食器應該就是“簋”,因為其形象與“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糧等主食的器皿,圓形,上面有蓋子,以便使食物保溫。《說文》:“簋,黍稷方器也。從竹,從皿。”這里以“方器”釋簋是錯誤的,從出土的青銅器來看,凡自銘為“簋”的器物大多為圓形,因此應釋為圓器。鄭玄注《周禮•地官•舍人》說:“方曰,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具體來說,簋的形狀很像大碗,一般為侈口、圓腹、圈足;或木制,或陶制,或以青銅鑄造。商代簋多無蓋,無耳或兩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較大發展,常帶蓋,有兩耳或四耳,間有帶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簋作為食器已經不很流行,只是在傳統的禮器體制中尚有發現,但形制有了較大變化。“簋”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或,字形的左半邊像簋中盛滿飯食,右半邊像手持匕匙、從簋中取食之形。《韓非子•十過》:“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可見簋是古人吃飯的主要用具。
對于“食”字的構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而上面的則像倒著的口,表示人張開大嘴趴在盛食器上來進食。這種說法似乎不太符合實際,因為“簋”這種盛食器有時候直徑可達幾尺,需要借助勺、匙之類的器具輔助,直接用嘴趴到簋上進食是不方便的。
“食”古代經常與“飲”連用,表示吃喝的總稱。《詩•小雅•綿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鄭玄箋:“渴則予之飲,饑則與之食。”可見,“飲”與“食”的分工是很明確的。“飲”甲骨文作,像人俯首吐舌、捧尊飲酒的形象。其中是人的身體,是酒壇子(即“酉”字),是倒過來的“舌”字。從字形來看,“飲”字的造字意圖本來是專指飲酒的。到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中,“飲”字形體中的酒壇子沒有了,而是變成了從水今聲的。由最初從“酉”發展到后來從“水”,說明“飲”已經不僅僅指“飲酒”了。到了周代,“飲”還發展出與酒相對立的意義:酒相當于今天所說的烈性酒,飲相當于今天所說的飲料。例如,《周禮》就專門設有酒人和漿人兩職,酒人掌管較為濃烈的酒,漿人則掌管所謂的“六飲”,包括水、漿(清酒)、醴(甜酒)等比酒淡薄的飲品。酒與飲的分稱,說明當時釀造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已經能夠控制酒味的厚薄,并詳細區分其等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