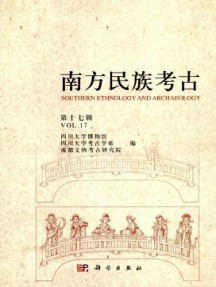地域文化的內(nèi)涵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3-09-19 15:26:5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地域文化的內(nèi)涵,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湘西苗族;舞蹈;文化內(nèi)涵
中圖分類號:J722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7-0160-01
湘西苗族舞蹈歷史悠久,它來源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在漫長的歲月中,苗族人民為了生存,在荒山野嶺之中過著原始的農(nóng)耕生活。在精神以及物質(zhì)生活極度貧乏的情況下,苗族人民仍然對幸福生活充滿了向往,在閑暇之余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民族的舞蹈藝術(shù)。這種舞蹈藝術(shù)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瑰寶,具有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
一、巫文化與湘西苗族舞蹈
湘西苗族人信巫好巫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他們擁有獨特而體系完備的巫教文化。對湘西苗族的民間舞蹈追本溯源可以發(fā)現(xiàn),其與巫在很久以前就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苗族舞蹈是原始表情手段的表現(xiàn)形式,從誕生之初就與苗族人的勞動、戰(zhàn)爭、娛樂密不可分,隨著它們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湘西文化之所以守成受動與當(dāng)?shù)刎毨У慕?jīng)濟環(huán)境是分不開的,而巫風(fēng)盛行就是其突出表現(xiàn)。湘西苗族舞蹈的動作、神態(tài)甚至裝飾都可以看到巫術(shù)行為的影子,此可謂“巫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可以說,湘西舞蹈與巫術(shù)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在原始氏族社會里,由于生產(chǎn)力低下,人們對自然界的某些現(xiàn)象缺乏準(zhǔn)確的認識,認為冥冥之中有神靈在主宰著一切。而人們又普遍希望遇事能夠逢兇化吉、轉(zhuǎn)危為安,于是開始求助于神靈,以歌舞作為娛神的手段,祈求神靈能夠賜福人間,對自己加以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教性的歌舞聚會,這也是歌舞表演最原始的狀態(tài),對于促進原始藝術(shù)的發(fā)展及走向成熟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對當(dāng)時社會的精神生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由于苗族舞蹈在苗族社會生活中漸趨物態(tài)化,一直到現(xiàn)在都與其社會習(xí)俗和糅合在一起。因此,難以從單個層面上來理解其中任何一種文化形態(tài)。有學(xué)者認為巫術(shù)是湘西苗族舞蹈的起源,這種看法雖然比較武斷,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出巫術(shù)與苗族舞蹈確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苗族民間舞蹈仍然比較純粹,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隨著社會日趨功利化,苗族民間舞蹈會出現(xiàn)一定的變化。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在湘西苗族巫術(shù)包括了一切,這是與其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分不開的。
二、耕獵文化與湘西苗族舞蹈
作為最早的農(nóng)耕民族之一,苗族早期活動于中原地區(qū)以及長江中游,在這里他們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繁衍子孫,開創(chuàng)文化。作為一個古老的農(nóng)業(yè)民族,苗族舞蹈也就很自然的與他們賴以生存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使其在崇拜活動中具有濃厚的農(nóng)耕色彩。湘西苗族舞蹈在表演內(nèi)容方面就記錄了其先祖的生產(chǎn)活動,質(zhì)樸的再現(xiàn)了他們的社會生活畫面。
農(nóng)耕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促進了農(nóng)耕文化的繁榮,民間舞蹈也因此應(yīng)運而生。最為直觀的是在湘西苗族民間舞蹈中,民間祭祀活動、原始獵獸場面以及慶祝豐收等情景屢見不鮮,有的舞蹈內(nèi)容還與獸類有關(guān)。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了解苗族民間舞蹈的發(fā)展歷程來獲知苗族農(nóng)耕文化的原始形態(tài)。苗族民間舞蹈無論是類型還是動作都取材于與農(nóng)業(yè)有關(guān)的日常活動,在這一時期,舞蹈風(fēng)格也不再像原始舞蹈那樣拙樸粗糙,而是漸趨華美和精致。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dāng)時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獲得了較大的發(fā)展。可以這么說,湘西民間舞蹈已經(jīng)成為反映苗族先民原始生產(chǎn)生活的一面鏡子。
苗族先民在遠古時代的生活以漁獵為主,隨著生產(chǎn)方式的逐漸演變,魚獵活動在經(jīng)濟生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這種風(fēng)俗卻得以世代相傳。探究眾多的魚獵文化活動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獵神崇拜作為苗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在魚獵生活中形成的。由此可知,魚獵生產(chǎn)在苗族人早期的經(jīng)濟活動中占據(jù)重要地位。農(nóng)耕時代開始之后,魚獵經(jīng)濟成為農(nóng)耕生產(chǎn)的重要補充,而其相應(yīng)的獵神崇拜習(xí)俗也沿襲下來。傳說在圍獵之前一般會有祭祀獵神的舞蹈,這種舞蹈就是苗族的木鼓舞。從表演形態(tài)上來看,苗族民間舞蹈具有線條粗獷、動作樸素的特點,同時也頗具野性。它來源于苗族先民原始的狩獵生活,反映了他們同自然作斗爭的堅強意志和樂觀向上的精神。從表演的動作和情節(jié)來看,苗族民間舞蹈蘊含著豐富的原始魚獵文化元素。
三、歌樂文化與湘西苗族舞蹈
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苗族民間舞蹈也在不停的發(fā)展和進步。苗族舞蹈在應(yīng)用方面不再局限于宗教祭祀活動,在各種傳統(tǒng)節(jié)日、婚喪嫁娶以及日常交往中也都能看到苗族舞蹈的表演,逐漸成為苗族人民交流情感、表達歡樂的群眾性舞蹈。
苗族民歌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早在戰(zhàn)國時期,屈原的《楚辭》就反映和表現(xiàn)了苗族先祖燦爛豐富且充滿神秘氣息的民歌文化。由此可知,民歌作為一種文化表現(xiàn)形式對文學(xué)、音樂、舞蹈、戲劇等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苗族先民有崇巫信鬼的文化傳統(tǒng),他們好歌好舞,有聲有色的表現(xiàn)了巫歌儺舞的藝術(shù)形式和特點。隨著歷史的進一步發(fā)展。苗族人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不僅在表現(xiàn)形式和表現(xiàn)內(nèi)容上獨具特色,而且還成功的將舞蹈和歌樂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歌、舞相得益彰的歌樂文化。它主要分為祭祀儀式和娛樂兩方面的內(nèi)容。
苗族的歌樂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它還是一種文化載體。作為苗族人民最為古老的藝術(shù)形式,它將歌樂與舞蹈有機的結(jié)合在一起。在湘西苗族地區(qū),尤其是群體場合,常常是歌舞相伴,唱和相繼,很容易形成熱烈的氣氛。
四、戰(zhàn)爭與湘西苗族舞蹈
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步中,戰(zhàn)爭始終如影隨形,戰(zhàn)爭已經(jīng)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給苗族人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從上古時代開始,苗族舞蹈就反映了各種各樣的戰(zhàn)爭場面,以武舞為主,文武糅雜是苗族傳統(tǒng)舞蹈的重要特點。苗族部落經(jīng)歷了從遠古時期到明清之際的無數(shù)次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歷史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苗族社會文化,必然與戰(zhàn)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舞蹈文化也是如此。如“猴兒鼓”活動據(jù)說就起源于部落戰(zhàn)爭時期,苗族先民用鼓聲來鼓舞士氣,激勵苗族勇士們奮勇殺敵。從這方面來看,苗族武舞以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形式對古代戰(zhàn)爭進行了敘述,從其動作姿態(tài)上來看具有很明顯的操練以及征戰(zhàn)性質(zhì)。
五、生、死與湘西苗族舞蹈
生死觀是人類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tài)度,不同的生死觀價值評價也不一樣,湘西苗族人的生死觀可以從“踩鼓舞”上得到充分體現(xiàn)。苗族人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地區(qū),平常爬坡上坎上山下山時,從他們的身體姿態(tài)、步調(diào)可以看出他們有一整套比較協(xié)調(diào)的習(xí)慣動作。諳熟苗族人生活規(guī)律和習(xí)慣的人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的行走特征隱含著“踩鼓”的韻律。一定的文化特征和習(xí)慣都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苗族人的這種行走韻律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是民族特征的自然流露。
不同民族對喪葬有不同的理解,在喪葬方式、喪葬價值觀上也存在區(qū)別。苗族在近代以來倡導(dǎo)土葬和洞葬,在停棺期間一般都要繞棺而舞,以“踏歌”、“鬧尸”的簡練方式表達一種長壽、吉祥的人生態(tài)度和境界。這種強有力的生命節(jié)奏能夠激蕩人的心靈,也表達了人類共有的心理傾向。
六、總結(jié)
綜上所述,湘西苗族舞蹈作為一種傳統(tǒng)民間藝術(shù),具有很強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寶。同時,湘西苗族舞蹈還具有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它是舞蹈與音樂藝術(shù)的完美結(jié)合,是社會歷史與人類情感的表現(xiàn)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以及藝術(shù)價值。
參考文獻:
[1]熊曉輝,鄭艷紅.湘西苗族民間舞蹈的文化本源[J].湖南文理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7(06).
篇2
關(guān)鍵詞:秦派二胡;作品;文化內(nèi)涵
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的積淀與發(fā)展,兼具西北地域特色與人文風(fēng)情的秦派二胡已成為二胡藝術(shù)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極具聲腔特色的演奏處理以及相對固定的曲韻曲體已使其具有了作為流派、學(xué)科進一步發(fā)展的可能。而本文試通過闡釋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內(nèi)涵,進一步豐富、拓寬秦派二胡的理論范疇,并為接下來秦派二胡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拋磚引玉。
一、研究現(xiàn)狀綜述
經(jīng)筆者的查閱搜集,其基本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是以秦派二胡為主題的論文,第二類則是以秦派二胡作品分析與研究為核心的論文,以下將對兩者進行具體分述。在以秦派二胡為主題的論文中,主要包括秦派二胡總體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秦派二胡代表人物創(chuàng)作與演奏研究這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較具代表性的是魯日融的《“秦派二胡”的形成與發(fā)展》,喬建中的《民族器樂地方派別的新景觀——從“秦派二胡”的生成與繁盛說起》,第二個方面,近些年來亦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秦派二胡代表人物的一系列研究,樸東升的《秦派二胡與魯日融》等、茍先維的《金偉秦派二胡藝術(shù)研究》,陳程的《李長春二胡藝術(shù)初探》等等。在以秦派二胡音樂作品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則主要是針對秦派二胡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展開——如《秦腔主題隨想曲》、《蘭花花主題隨想曲》、《秦風(fēng)》等等。此類文獻研究視域包括演奏技巧與體會、藝術(shù)特色兩大方面,并已呈逐年遞增態(tài)勢。
二、管窺秦派二胡作品的地域文化內(nèi)涵
作為文化的具體承載,任何藝術(shù)作品都不能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這點在音樂作品中體現(xiàn)更為明顯。不同地域、民族之間,其音樂作品的形態(tài)注定也會存在諸多不同。從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角看,秦派二胡的發(fā)展亦不能離開獨具特色的陜西地域特色與精神特色,以下,筆者將通過對秦派二胡的地域文化內(nèi)涵,進一步闡釋秦派二胡所獨具魅力的文化性。從地域角度看,陜西地處西北要道,兼有黃土高原與關(guān)中平原,疊嶂與沃野,賦予了陜西以娟秀而壯麗的山川景致,在此之下,其音樂亦具有醇厚、粗獷的特點。這點在地域的“名片”——戲曲音樂方面猶有突出表現(xiàn),比如秦腔、碗碗腔等獨特的劇種便馳名中外。人們喜愛陜西的戲曲音樂,并不僅僅是因為其獨特的聲腔韻律,亦是因為其具有撲面而來的中國大西北粗獷而別具一格地域文化特色。而從秦派二胡作品與戲曲音樂的關(guān)系來看,可以說,秦派二胡創(chuàng)作亦牢牢依附于戲曲音樂,乃至大西北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魯日融先生曾說,“中國的西北主要是黃土高坡,在這樣的地理環(huán)境下,民間音樂,尤其是歌曲都是比較高亢的。”而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秦派二胡作品可謂深具地域三昧。比如秦派二胡的經(jīng)典之作《秦腔主題隨想曲》,其素材便與秦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樂曲開始的第一段便取材于秦腔曲牌《殺妲姬》,其尾聲則采用秦腔曲牌中“扭門栓”的旋律。而在魯日融另一首敘事曲《曲江吟》中,則選用了陜西地方戲曲音樂中的迷糊和碗碗腔作為創(chuàng)作素材。而在我們審視數(shù)量眾多的秦派作品中,亦會發(fā)現(xiàn):其中大部分音樂作品雖呈現(xiàn)出百花爭鳴的具體形態(tài),但其中對戲曲音樂的借鑒所呈現(xiàn)出的,西北所獨具的地域文化特色,則是清晰可見的。另外,從音樂作品的處理上,我們亦可以感受到深刻的秦地、秦人的獨特風(fēng)貌。比如,在對音階的運用上,秦派二胡作品常常出現(xiàn)“歡音(微降si,微升fa)”與“苦音(mi,la作為骨干音)”,從而使作品具有陜特的聲韻特色。再如,從秦派二胡更為具體的演奏處理上看,比如在大量作品中出現(xiàn)的摟弦、壓弦以及回滑音、上滑音的特殊位置等等,則使作品本身呈現(xiàn)出獨特的歡樂與悲苦。很難想象,當(dāng)這種陜具特色的演奏手法運用到南方音樂作品中會出現(xiàn)怎樣的發(fā)展——或者說,秦派二胡的演奏手法,正是其本身形成為一個流派的所依所靠,這正是其區(qū)別于其他流派的鮮明特色。而亦是這種獨特的精神表達,使秦派二胡作品形成了其獨具的魅力與意義。秦派二胡的發(fā)展離不開對陜西文化的持續(xù)關(guān)注與思索,換言之,只有保持地域?qū)徱暭捌洫毺氐木駥徱暎拍苁龟兾鞯囊魳纷髌贰M而是秦派二胡的研究與發(fā)展實現(xiàn)一個又一個跨越與發(fā)展。而從這個角度看,本文對秦派二胡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與精神文化內(nèi)涵的關(guān)注僅僅是一個開始,亦是一個啟示——在傳承秦風(fēng)秦韻時,不可只砥礪樂既,亦需砥礪樂思——思索秦派之秦韻、思索秦派所獨有的文化內(nèi)涵,唯此,可期千里之行。
[參考文獻]
[1]魯日融.“秦派二胡”的形成與發(fā)展.交響(西安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1,01.
[2]喬建中.民族器樂地方派別的新景觀——從“秦派二胡“的生成與繁盛說起.人民音樂,2010,10.
[3]牛苗苗.秦派二胡的專業(yè)教學(xué)與學(xué)科建設(shè).樂器,2009,05.[4]李寶杰,王青.秦派二胡藝術(shù)的文化闡釋.星海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1,03.
[5]樸東升.秦派二胡與魯日融.人民音樂,1998,07.
篇3
關(guān)鍵詞:天水旋鼓;民間藝術(shù);伏羲文化;民俗文化
天水籍詩人何俊秋先生觀看天水旋鼓的表演后,有感于那磅礴的氣勢和藝術(shù)感染力,揮毫寫下這樣的詩句;
中華名鼓多,秦州旋鼓殊。羊皮蒙面俏,鐵骨鳴環(huán)輔。
旗開劃天式,陣列八卦圖。平擂山川震,側(cè)擊云飄浮。
低垂成壁壘,高托把天補。猬集聲漸漸,迸發(fā)誰能阻。
方瞻伏羲祭,忽見秦俑舞。龍城飛將至,充國又勝胡。
佛哉人文地,惜乎此明珠。一朝擊潼關(guān),當(dāng)驚世界殊。
詩人在詩中精彩的解讀了天水旋鼓的文化內(nèi)涵,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對主要動作和隊形中蘊含的伏羲文化內(nèi)涵及地域特色作了恰當(dāng)?shù)谋扔骱托稳?引導(dǎo)觀眾一同來領(lǐng)略旋鼓獨具魅力的藝術(shù)風(fēng)采,理解其豐厚的文化底蘊。
天水,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華夏先祖在這里以辛勤的勞動和智慧,創(chuàng)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伏羲文化、大地灣文化、龍文化、贏秦文化、石窟文化、三國文化在這里大匯聚。相傳,中華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伏羲就誕生在這里,以伏羲時代為標(biāo)志,中華民族擺脫了洪荒時代的昧,探索發(fā)明了新的生產(chǎn)手段和生活方式,為中華民族早期的文明和興旺發(fā)達奠定了根基,天水已成為全球華人尋根祭祖的圣地。
天水風(fēng)物秀美,人文薈萃,文物遺存豐富,民俗風(fēng)情獨具風(fēng)韻。她以其璀璨的歷史文化和眾多的名勝古跡而蜚聲中外,更以其豐富多彩、地域特色濃郁的民間民俗文藝享譽隴上;蠟花舞、高搖傘、鞭桿舞、秦州夾板等民間藝術(shù),就象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鑲嵌在美麗的天水大地上,熠熠生輝,相映成趣。“天水旋鼓”就是根植于這塊民間文藝沃土之上的奇葩,它與其它民間、民俗文藝形式交相輝映、爭奇斗艷,得以使隴原大地文化藝苑姹紫嫣紅,分外妖嬈。
一、旋鼓的起源與傳說
“旋鼓”主要流傳于甘肅省天水市轄區(qū)武山縣的灘歌、山丹、百泉、龍泉、龍臺、馬力、新觀寺、南峪等鄉(xiāng)鎮(zhèn)。旋鼓從其質(zhì)地看,鼓面用羊皮蒙制,故也稱“羊皮鼓”。從其形狀看,形似一個大蒲扇,也叫“扇鼓”。由于最初是在山頂上點著堆積如山的柴火,大家圍著火堆敲起旋鼓而翩翩起舞,因而民間又稱其為“點高山”或“迎高山”。再從其隊形變化和動作特點看,旋轉(zhuǎn)多變,猶如旋風(fēng)一般起舞,又因在民間表演時各路鼓隊相互擠推碰撞、相互裹挾盤旋,取其旋轉(zhuǎn)與盤旋之意,故而稱之為“旋鼓”。
據(jù)旋鼓誕生地相傳,旋鼓是由羌族人發(fā)明的,曾經(jīng)在武山、甘谷一帶生活著勤勞智慧的羌民族,羌族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優(yōu)秀的民族之一,而且是最早進入農(nóng)牧兼營,早期羌人的生產(chǎn)方式也經(jīng)歷了以畜牧業(yè)為主的階段,并且特別鐘愛對羊的飼養(yǎng)。從語言學(xué)角度而言,我們今天稱之為“羌族”的“羌”是屬他稱,“羌”字從羊、從人,意為“西戎牧羊人”。歷史上它是以養(yǎng)羊著稱于世的民族,故羌族與羊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在羌族聚居地,至今仍保留著供奉“羊神”的習(xí)俗,羌人稱羊神為“卡掐”,是村民家中供奉的十二家神中的一個,他們認為羊神負責(zé)管理六畜,六畜的平安興旺均由其管轄。由于羌人與羊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和對羊有極強的崇拜心理,那么,羌族人發(fā)明“羊皮鼓”也是順理成章的。
在武山當(dāng)?shù)匾恢绷鱾髦裂蛉税l(fā)明旋鼓的傳說:在很久以前,有一牧童,常年在外放羊,出沒于人煙稀少的荒郊野嶺之中。由于惡狼常常把羊叼走,飽受惡狼之害的牧童,機智勇敢地與狼展開了周旋和搏斗。他觀察到每年四月前后是狼產(chǎn)仔的季節(jié),聰明伶俐的牧童便在高山頂上點燃火堆,打起自制的羊皮鼓,圍著火堆旋轉(zhuǎn)起舞,火光照亮山川,鼓聲響徹云霄,以此恐嚇惡狼,震死狼仔。從此,只要一聽到鼓聲和見到火光,狼就不敢再來侵擾,“點高山”、“迎高山”也就由此而得名。
有學(xué)者考證認為,旋鼓的出現(xiàn)可遠推上古,近至夏代,“旋”,古人稱天為旋或玄,旋鼓即天鼓,所以在旋鼓鼓面上常繪有太極圖。
二、天水旋鼓獨具豐富的伏羲文化內(nèi)涵
從天水旋鼓的動作和步法移動來看,鼓手多以單S形、螺旋形或雙S形前行,隊形也有“蛇搜道”、“一字長蛇陣”、“旋蝸牛”等,這種行走路線應(yīng)該是模仿蛇行之“禹”步,隊行變化如游蛇蜿蜒,湖南巫師稱其為“踩八卦”,據(jù)說“踩八卦”之“禹”步是夏禹祭祀祖先的舞步。在表演中還加入了“師公”甩“蟒頭”的內(nèi)容,就是讓表演者在發(fā)套上帶上長發(fā)辮不停甩動,當(dāng)?shù)厝朔Q之為甩“馬頭”。筆者認為稱之為“蟒頭”更為確切,因為蟒與蛇形體相似,傳說中伏羲是人面蛇身,因而在旋鼓表演中甩“蟒頭”的彩色發(fā)辮是人面蛇身的扮相,隊形變化也暗含對伏羲的祭祀與敬重。此外,在表演中還不時聽到鼓手發(fā)出“噢噢”、“嗨嗨”的喊叫聲。聞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中描述了祖先的圖騰祭祀場面;鼓手腦后束辮正是人面蛇身的扮相,舞步、隊行、呼嘯是對蛇的舉動的模仿,以期獲得祖宗的認同和庇護。在伏羲文化的精神里,最本質(zhì)的內(nèi)容是崇尚自然,它包含了人們揭示自然規(guī)律并遵循自然規(guī)律改造自然的哲學(xué)思想,因而,旋鼓的表演要從內(nèi)容到形式相統(tǒng)一,在動作形態(tài)上自然隨意,不留匠斧痕跡。在表演氣質(zhì)上充分體現(xiàn)伏羲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內(nèi)涵,追求自不息、百折不撓、努力進取、剛健有為的精神,以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主導(dǎo)人生,充滿生命的活力。在表演風(fēng)格既“鼓風(fēng)”上,力求體現(xiàn)出自然雄渾的氣勢、沉穩(wěn)豪邁的步履、堅韌執(zhí)著的神態(tài)和粗獷豪放的品質(zhì)。
天水旋鼓在服裝、道具設(shè)計上既尊重旋鼓起源的各種傳說,又盡可能體現(xiàn)出了天水的文化背景,融入伏羲文化的內(nèi)容,在鼓面圖案上特別突出了“太極八卦”圖形,這與伏羲文化緊密相聯(lián),在甘肅境內(nèi)乃至全國流傳的各種鼓幾乎都繪有太極八卦圖這一古老的哲學(xué)符號。表演陣形多涉及“八卦陣”,表演人數(shù)也往往要湊足64位,以合“六十四”卦之意,因為始作八卦的人類始祖伏羲就誕生在這里,“羲皇故里”的人們特別鐘情于“八卦”的思維意識充分說明,擂起鼓而變“八卦”觸陰陽,“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紋,興地之宜,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充分表露出天、地、人、鼓合而為一的思想,成為鼓舞起始的“心象”特征。
三、天水旋鼓彰顯地域特色及人文精神
天水旋鼓的服裝設(shè)計為黃色,寓意來自廣袤的黃土地,服裝圖案整體展現(xiàn)了“龍”形,隊形變化有“龍擺尾”、“二龍戲珠”等,這也蘊涵了圖騰舞蹈的特點。相傳天水是“龍”的故鄉(xiāng),素有“龍城”之稱謂,龍,代表了力量、活力、熱情、無懼以及專注。對于龍文化的展示,不只是在天水旋鼓中展示,在甘肅境內(nèi)流傳的眾多鼓舞中隨處可見,在鼓身常繪有“二龍戲珠”的圖案,在隊形變化中有“龍擺尾”,儀仗中有“龍旗”。天水旋鼓在服裝設(shè)計上抽象地體現(xiàn)了“龍鱗”、“龍爪”、“龍首”的元素。中華龍形象神奇,是先民們集合許多動物及某些天象的形貌特征,經(jīng)過漫長歲月創(chuàng)造出來的靈物,是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圖騰,主要象征正義與吉祥,而在旋鼓中之所以特別突出龍的形象,意在融合團結(jié)、創(chuàng)新、奮進這一龍文化的顯著特征,從而使鼓舞達到形神兼?zhèn)渲康摹?/p>
天水旋鼓源于“武山旋鼓”,武山在歷史上也是戰(zhàn)略要地,素有“秦隴噤喉,巴蜀鎖鑰,屯戎要塞”之稱謂,距今約38000年前的“武山人”頭蓋骨化石就出自這里。武山人崇武尚武之風(fēng)盛行,從旋鼓表演的風(fēng)格中也突顯了他們勇猛與強悍的個性品質(zhì)。歷史悠久的天水旋鼓反映出人們在與自然界的斗爭中所發(fā)揮出的聰明才智,也可以說鼓是黃土地上的人們精神氣質(zhì)的載體和外化介質(zhì),這種精神載體,不僅傳遞著祖先遺留的文化信息、包含了引人入勝的神秘色彩與歷史沉淀,它更體現(xiàn)了人類文明與歷史演進中那些最為光彩美好的東西。在民間民俗文化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由于自然景觀、人文特質(zhì)的差異,催生了風(fēng)格迥異的文化形態(tài),它根植于中國特有的農(nóng)耕生活,并從中生長出來,其最基本的特質(zhì)就是農(nóng)耕生活的基本欲求和人天關(guān)系中什華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農(nóng)耕信仰。
任何文化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發(fā)展都不是隨意或孤立的,一個民族的文化方式或生活方式總是體現(xiàn)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現(xiàn)象也隱含著一個民族文化的生命信息和遺傳密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nèi)核是群體意識,而天水旋鼓所傳遞出的信息,從根本上說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種群體精神風(fēng)貌,極具內(nèi)聚力。中國鼓文化豐富多彩,由于其流傳區(qū)域的不同,鼓舞的風(fēng)格也有很大差異,在我國一般北方地區(qū)鼓風(fēng)威武樸實,雄壯有力,南方地區(qū)鼓舞抒情優(yōu)美,充滿田園風(fēng)光,而地處西南邊陲,身處崇山峻嶺之中的少數(shù)民族鼓舞充滿著古老而神秘的色彩,獨具民族特色。它是中華民族精神在藝術(shù)方面真正的象征,是尚存在廣大民間一筆極可貴的藝術(shù)遺產(chǎn),是我國一份極有價值的、充分表現(xiàn)中華民族富有元氣精神的寶貴文化藝術(shù)財富,在當(dāng)今更應(yīng)該發(fā)揚光大。
參考文獻
[1]郭承錄.武山史話.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
[2]曹昌光等編著 羲皇故里天水游.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篇4
論文關(guān)鍵詞:陜北 陜北方言詞語 地域文化
序言
歷史上,漢語形成了多樣、復(fù)雜的方言。陜西北部,即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區(qū)域,包括延安、榆林兩個地級市,通行著陜北方言。陜北方言詞語是指陜北方言中的詞和熟語的總和,是陜北方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學(xué)者李光庭說:“言語不同,系乎水土,亦由習(xí)俗……”可見一定的語言與當(dāng)?shù)氐牡乩憝h(huán)境、地方習(xí)俗、傳統(tǒng)觀念等直接相關(guān)。陜北方言詞語中有大量的地名詞語,這些詞語往往反映了當(dāng)?shù)氐牡乩砻婷病v史演變和人們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討陜北方言地名詞語所反映的區(qū)域地貌特征和所積淀的陜北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內(nèi)容。
一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的區(qū)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間中,就不能不與反映空間地理位置的地名詞語打交道。陜北方言詞語中,地名的詞語相當(dāng)活躍,成為當(dāng)?shù)厝巳粘I畈豢扇鄙俚牡闹匾M成部分。地名詞語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專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詞語大多反映了當(dāng)?shù)刈匀坏乩淼孛蔡卣鳎鴮C糠謩t反映了當(dāng)?shù)匚锂a(chǎn)特點。
1 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地理特征
陜北在地理上屬于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qū),在地貌上表現(xiàn)為溝壑縱橫,峁梁相接,溝峁交錯的特點。陜北人在給地理實體起名時多以“溝”、“墕”、“岔”、“崖”、“畔”作為通名。反觀之,這些通名記錄反映了陜北溝壑峁梁眾多的區(qū)域地理地貌特征。
溝:山溝,地面低洼地帶。陜北溝壑眾多,以“溝”命名的地名詞語也很多,如子洲的宋家溝、曹家溝等。
含:兩山相連處,俗稱“含”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區(qū)。如子洲有米家、佟家,府谷有王家。
岔: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為名的有:綏德的霍家岔、清澗的岳家岔、子長的青陽岔等。
崖(陜北方言讀nai):山邊陡峭處。帶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綏德的李家崖等。
畔:黃土山體的旁邊或附近。住在土山側(cè)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杜家畔,靖邊的張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邊的地方則稱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峁:頂部渾源、斜坡較陡的黃土丘陵。以“峁”為名的地名象神木的沙峁,子洲的拓家峁等。
梁:山體中間隆起的地方。以“梁”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溫家梁、榆陽區(qū)的李家梁等。
圪嶗:山間避風(fēng)處,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嶗,洛川有王家圪嶗、史家圪嶗。
圪凸(陜北方言讀du, 上聲):山間突出處。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澗的師家圪凸,吳堡的樊家圪凸等。
崾峴:山上或平川地勢險要地段。崾峴也寫作崾險。如榆林的孫克崾峴、安塞的佛道崾峴等。
坪:黃土丘陵或山區(qū)中的平地。綏德有棗林坪、子洲有苗家坪等。
咀: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環(huán)溝的地方或村莊。綏德有魚家咀、安家咀。清澗有石咀驛鎮(zhèn)。
其實上述地名不為陜北所獨有,全國各地都有分布。不過,由于受到陜北區(qū)域地理地貌的影響,這種情況在陜北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我們在觀看陜北地圖時會強烈感受到這一點。
2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當(dāng)?shù)氐奈锂a(chǎn)
地名不僅是當(dāng)?shù)氐匦巍⒌孛驳男蜗笤佻F(xiàn),同時通過地名也反映了當(dāng)?shù)貐^(qū)域物產(chǎn)特點。
榆林因其多種榆樹而得名。類似的還有安塞的榆樹灣、志丹的榆樹窯子、橫山的榆樹峁等。
佳縣(原名葭縣)因縣境內(nèi)有一條葭蘆川,葭蘆叢生得名(古人把葦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蘆,長成后的叫葦)。府谷有野蘆溝。
米脂,因境內(nèi)有米脂水而得名。米脂水,又名流金河,此地水土肥沃,盛產(chǎn)小米,質(zhì)醇味美。史書上說米脂水“沃壤空粟,米質(zhì)如脂”,因而在宋代首建米脂寨。
甘泉縣名最早始于唐代,以縣南谷崖有泉水“飛流激下,甘甜美味,隋煬帝游山時曾汲取”而得名。
陜北各地都有棗樹種植,因此以棗林、棗樹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綏德有棗林坪、綏德的棗樹灣、安塞有棗樹臺,志丹有棗林坡。
其他植物在陜北也多有栽種,如柳樹、槐樹,梨樹、桑樹、柏樹、桃樹、海紅等。以此命名的如:安塞有柳林鎮(zhèn)、柳灣,榆林有紅柳溝鎮(zhèn),定邊有柳樹梁、紅柳溝;安塞有槐樹莊,志丹槐樹臺,子洲有槐樹岔;安塞有梨樹溝;府谷有圪針?biāo)?府谷有桑林坪、桑園梁;府谷有柏樹峁;綏德有桃樹峁;府谷有海紅梁等。
在陜北各地反映動物的地名不多。陜北各地有雉雞,這在地名中有反映,如定邊的金雞灣、金雞灘,這里的金雞疑為雉雞的方言改稱,另外如榆林有野雞河等。
榆林的上鹽灣、下鹽灣,也因其盛產(chǎn)鹽而得名。此外從靖邊:寧條梁鎮(zhèn)、黃蒿界鄉(xiāng)、席麻灣鄉(xiāng),清澗的石盤鄉(xiāng)等地名都可了解當(dāng)?shù)氐奈锂a(chǎn)特點。
二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的文化內(nèi)涵
1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古代民族接觸
陜北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要地。歷代王朝為了爭奪陜北這塊地區(qū),長期頻繁進行拉鋸戰(zhàn)。戰(zhàn)爭之后,陜北漢民族人民與匈奴、鮮卑、突厥、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人民融合雜居、交流交往,這些為陜北文化注入了豐富而獨特的文化內(nèi)涵。
在古代,陜北曾是少數(shù)民族活動的舞臺。宜川縣有庫渦川、延安有庫利川、延長有渭牙川,便是匈奴語“庫渦、庫利、渭牙”,加漢語通名“川(chuan,按陜北方言讀上聲)”命名的。
陜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區(qū)接近內(nèi)蒙,地名命名多受蒙語影響。這些地名多分布于靠近內(nèi)蒙古的村莊。此外,還有蒙語地名加漢語方位詞或通名形成的地名,如神木的大保當(dāng)(灌木叢草灘)、中雞等,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歷史上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雜居相處,互相學(xué)習(xí),相互交流的民族融合局面。
伙盤指清代農(nóng)民租種蒙旗土地的地方,也作“火盤”,因而也有以此命村名的。榆林有白家伙場、郭家伙場,神木有鐵匠伙盤、楊伙盤,這些地名反映了漢蒙交往的史實。
另外,還有一些受其他少數(shù)民族姓氏影響的地名。如與歷史上北魏時期的鮮卑族活動有關(guān)的乞佛(洛川縣朱牛鄉(xiāng)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等。歷史雖已遠去,但地名這一活化石卻鐫刻了民族融合的情景并把它頑強地保留到今天。
2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陜北古代軍事
在我國歷史上,整個西周階段,陜北地區(qū)基本上是被獫狁占據(jù)著,秦漢時期陜北屬上郡所轄,而上郡在當(dāng)時的軍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東漢末年,陜北則為匈奴等族占據(jù),隋唐時代,陜北曾是突厥部族活動的地區(qū)。宋金元明時期,陜北是國家的軍事要沖,邊防重鎮(zhèn),歷代王朝為了這塊地區(qū),曾付出了很大代價。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在長城沿線設(shè)置榆林衛(wèi),筑“邊墻”,設(shè)城堡,從含有“鋪,驛”、“墻、城、堡”的陜北方言地名詞語中則可以看出古代在軍事防御方面的布局。
宋時為防御突厥、西夏,在沿邊地帶擇沖要處建立一系列城、寨、營、堡組成的防御體系,含有“墻、城、堡、寨”的地名,可以追溯到宋代。地名中的“墻”即指長城。含有“城”的地名,由于時代的原因,有的城址已廢,但其輪廓仍然清晰,成為陜北的名勝古跡。如統(tǒng)萬城(靖邊),又名“白城子”,曾是東晉時匈奴族首領(lǐng)赫連勃勃建立“大夏國”的都城;楊家城(神木),即古麟州城,為古代邊塞著名的軍事堡壘。陜北地名中有鐵邊城,五谷城(吳旗)、朱官寨(佳縣),新寨(吳起),太和寨(神木),張家寨(子洲),高家堡、欄桿堡(神木),響水堡(宜川)、安邊堡(定邊)、解家堡(神木)、榆河堡、龍州堡、歸德堡、雙山堡(榆林)、波羅堡(橫山)等,這些地名有些是宋代設(shè)立的。從這些地名,我們可以看出古代軍事防御體系的布局設(shè)置。
3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寧的心理和宗教信仰
詞語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詞語的使用和演變可以映射出陜北人民的文化心理。陜北地名詞語突出反映了歷代當(dāng)?shù)鼐用衿砬蟀矊幍男睦恚从沉怂麄兊淖诮绦叛觥?/p>
陜北地名詞語反映官民渴望“安寧,安定”的愿望。陜北方言地名中的含有“安”“寧”“綏”等詞語集中反映了厭惡戰(zhàn)爭,祈求安寧的心理。如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安邊、順寧、撫寧、安民(延川)、定邊、靖邊、綏德等。
類似這種借地名詞語表達人們美好愿望的,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如陜北地名中的吉利坪、豐富莊等,都是用含有吉祥如意的詞語表達美好心愿。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中還滲透有錯綜復(fù)雜的宗教信仰,至今遺留下的佛教、道教有關(guān)的地名即是有力的證據(jù)。如黃龍小寺莊,因宋時佛教寺院圣壽寺而得名;延安市的石佛溝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此外還有神樹塔、神樹溝(神木)、龍王廟(府谷)、長官廟(吳旗)、老爺廟(定邊)等,這些詞語則與陜北當(dāng)?shù)氐腻e綜復(fù)雜的民間信仰有很大的關(guān)系。
4 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
陜北大部分地區(qū)地處山區(qū),其獨特的地理風(fēng)貌與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蘊藏于古老的陜北方言詞語中。由于自然條件差,又多受干旱、風(fēng)沙、鹽堿等多種自然災(zāi)害的威脅,人們的房屋多建于山邊或山間避風(fēng)處,生活異常艱苦,習(xí)慣稱勞動為“受苦”,把莊稼人稱做“受苦人”。如綏德的碌碡峁,安塞的鐮刀灣等將古老的傳統(tǒng)農(nóng)具蘊涵于地名中,反映了生活在陜北黃土地的人以農(nóng)耕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像延安的韓家窯子、任家窯子等以“×窯子”命名的地名在陜北很常見,從中可看出某地最初入住的居民的情況,以及人們居住以窯洞為主,居住地比較固定的生活特點。
5 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習(xí)俗
“×家”格式的地名詞語在陜北各地普遍存在。如清澗的李家坪,綏德的李家崖,子洲的汪家崖、杜家畔、馬家石畔、苗家坪、周家圪嶗,靖邊的張家畔、拓家峁,米脂的井家畔,清澗的郝家畔,府谷的蘇家畔,橫山的王家峁,榆陽區(qū)的李家梁,清澗的李家坪,洛川的王家圪嶗,等等。
中國人自古就重宗族,重血緣,有親屬或宗族關(guān)系的人往往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以宗族的姓氏作專名,加上反映該村落地理特點通名的地名全國各地都有。陜北,地理條件差,自然條件惡劣,加之地廣人稀,社會經(jīng)濟十分落后,這就需要同宗族的人互相照應(yīng),共同應(yīng)對各種困難。所以,在陜北各地,象李家坪這樣的地名非常多。作為語言,類似的地名強化了陜北人的地緣關(guān)系,陜北同族或同村或同地域的人特別抱團,老鄉(xiāng)觀念非常濃厚。當(dāng)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居民的移遷,聚居在一起的人未必都有宗族或血緣關(guān)系了,居住習(xí)俗也發(fā)生了變化,但地名詞語卻頑強地存在下來,從而把祖先們聚族而居的生活習(xí)俗記錄下來,流傳了下來。
三 結(jié)語
方言地名詞語作為社會生活以及人文環(huán)境物化的代號,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通過探索方言地名詞語,從中可以揭示內(nèi)涵豐富的、獨特的地域文化。
陜北方言地名詞語與陜北地域文化二者關(guān)系密切。一方面,陜北方言詞語反映著陜北地域文化,透過它可以了解本地域種種文化現(xiàn)象,包括歷史交往、地理環(huán)境、生活生產(chǎn)習(xí)俗、宗法觀念、思維方式等。另一方面,陜北文化對陜北方言詞語的形成、運用和發(fā)展演變有著深刻的影響。比如陜北的榆林明清之際作為邊塞,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榆林城里的老年人罵人:看你哪個囚犯腦袋。別的地方的人則很少有這種罵人法。總之,研究陜北方言詞語與陜北地域文化的關(guān)系,可以使我們深刻領(lǐng)會語言和文化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注:本文是陜西省教育廳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07JK15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劉育林:《陜北人學(xué)習(xí)普通話教程》,1993年。
[2]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呂廷文:《淺議陜北地名與陜北古代文化》,《延安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1995年第2期。
[4] 尤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xué)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篇5
關(guān)鍵詞: 地方文化 綜合實踐活動 人文氣質(zhì) “走近顧炎武”
新課標(biāo)實施至今已經(jīng)超過十個年頭,在這期間,對語文學(xué)科性質(zhì)的討論與認同始終貫穿其中。雖然在語文學(xué)界提倡人文性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作為一個高中語文教師,我有感于教學(xué)實踐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深刻感受到高中語文教學(xué)越來越滑向應(yīng)試化、機械化、工具化的深淵。如何讓語文教學(xué)充滿人文主義的關(guān)懷是每個語文教師不得不直面和思考的課題。
我的家鄉(xiāng)昆山是一座充滿靈秀氣息的江南水鄉(xiāng)城市,這里物產(chǎn)資源豐富,歷史文化悠久,是“百戲之祖”昆曲的發(fā)源地,千年古鎮(zhèn)周莊被譽為“中國第一水鄉(xiāng)”。豐富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充滿了濃厚的人文氣息。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昆山人,我工作、生活在這里,熱愛昆山文化,熟悉昆山的教育現(xiàn)狀,渴望對地方文化資源開發(fā)做出有意義的探索和實踐,并把它們滲透到教學(xué)中,以此提升語文課堂的人文氣質(zhì),使學(xué)生在文化的濡染和熏陶中吸收知識,傳承文化,培養(yǎng)能力,提高人文素養(yǎng)。
一、活動設(shè)計
(一)實施理念
綜合實踐活動指在語文教學(xué)的過程中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查閱資料、閱讀評價、撰寫文章等一系列活動,豐富學(xué)生的情感體驗,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審美情趣,從而培養(yǎng)和提高學(xué)生的閱讀分析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的綜合教學(xué)活動。綜合性教學(xué)實踐活動是新課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課標(biāo)》指出:“在閱讀與鑒賞活動中,不斷充實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對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思考和認識。”恰當(dāng)?shù)亻_展綜合性教學(xué)實踐活動,可以大大拓寬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空間,以此培養(yǎng)學(xué)生主動探究、團結(jié)合作、勇于創(chuàng)新的個性精神,使學(xué)生更多地關(guān)注社會、關(guān)注生活。
(二)活動預(yù)期目標(biāo)
1.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理性、辯證地評價顧炎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精神;了解顧炎武“經(jīng)世致用”的哲學(xué)思想,評價他的哲學(xué)思想對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
2.在調(diào)查研究和交流展示過程中培養(yǎng)學(xué)生團隊合作的能力和專題研究的能力,激發(fā)學(xué)生對地方文化的興趣,喚起學(xué)生對家鄉(xiāng)文化建設(shè)的珍視,在生活學(xué)習(xí)中以實際行動來保衛(wèi)地方傳統(tǒng)文化建設(shè)。
(三)資料鏈接
1.人物介紹:顧炎武(公元1613——1682),江蘇昆山人,是明清之際杰出的思想家、史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明季諸生,青年時發(fā)憤為經(jīng)世致用之學(xué),并參加昆山抗清義軍,敗后漫游南北,曾十謁明陵,晚歲卒于曲沃。學(xué)問淵博,于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nóng)及經(jīng)史百家、音韻訓(xùn)詁之學(xué),都有研究。晚年治經(jīng)重考證,開清代樸學(xué)風(fēng)氣。
2.酬王處士九月見懷之作(2008年北京卷詩歌鑒賞)
顧炎武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
離懷消濁酒,愁眼見黃花。
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
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3.亭林先生神道表清全祖望(南通市2010屆高三第二次模擬考試)略
4.《昆山文史選集》、《昆山縣志》、《昆山禮贊》、《三賢詩文精編選》、《傳是樓集》等圖書館藏資料。
(四)活動步驟
第一階段:在老師的指導(dǎo)和帶領(lǐng)下,分小組前往昆山亭林公園顧炎武紀念館實地考查,赴昆山圖書館查找相關(guān)資料,利用網(wǎng)絡(luò)查找顧炎武生平及著述的相關(guān)資料。
第二階段:學(xué)生根據(jù)研究調(diào)查情況對顧炎武生平事跡或著述文章寫調(diào)查總結(jié)。
第三階段:各組進行評價、展示和交流,并舉行研討會,匯報交流研究成果。
第四階段:老師對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給予肯定,對一些富有啟發(fā)的有意義的研究成果進行后續(xù)調(diào)查并總結(jié)評價。
二、分析評價
地方文化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怎樣把它潛在的文化價值發(fā)揮到最大化,在本次綜合教學(xué)實踐活動中,地方文化在整個教學(xué)活動中承擔(dān)怎樣的角色,如何評價地方文化在提升語文教學(xué)人文氣質(zhì)中起到的作用,怎樣通過了解地方文化提升學(xué)生的文化品位,這些問題是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并深入思考的。語文教師要善于在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充分認識文化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把對地方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貫徹到教學(xué)實踐中,在閱讀和鑒賞中,引導(dǎo)學(xué)生不斷充實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思考和認識。①
(一)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先賢來提升學(xué)生的文化品位